- 1Dipartimento di Psicologia,UniversitàdegliStudi della Campania Luigi Vanvitelli,Caserta,Italy
- 2英国诺丁汉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心理学系
背景: 尽管对游戏障碍(GD)的研究数量有所增加,但评估临床受试者的特征仍然有限。 在克服这一局限性的需要的驱动下,广泛的系统评价对于已经评估了已诊断患有GD的个体的临床特征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目标: 本系统评价的目的是提供广泛的跨文化图片,了解GD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的当前诊断程序和干预措施。
方法: 共有28研究符合纳入标准,数据合成这些类别:(1)研究所在国家的文化背景; (2)用于测量GD的仪器; (3)GD的诊断标准; (4)使用的诊断程序; 和(5)应用的治疗方案。
结果: 该系统评价的结果表明,在GD临床实践中,仪器的选择,GD的诊断和干预过程存在大量异质性。
结论: 该系统评价表明,GD的临床人群中标准程序的验证过程对于为从业者创建明确的共享指南是必要的。
介绍
合理
电子游戏的使用是全世界迅速增长的现象,涉及所有年龄组的人。 游戏平台(例如专用控制台,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多样性以及需求的增长促使游戏行业成为最赚钱的娱乐行业之一(Kuss等人,2017)。 与互联网技术的整合进一步扩大了视频游戏的使用范围,使游戏体验更具吸引力和沉浸感。 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和多人在线战斗竞技场(MOBA)是在沉浸式和挑战性环境中结合社交互动的典型游戏示例。 虽然游戏是一项愉快的活动,也可以提供有趣的教育意义(De Freitas和Griffiths,2007; Hainey等,2016),对于少数玩家过度游戏可能导致传统上与物质相关的成瘾相关的症状的发展。 虽然游戏只是少数倾向于过度玩耍并产生消极症状的人的风险活动,但公众对“沉迷于游戏”的恐惧已经通过媒体普及,这反过来激发了对卫生政策的争论因为游戏是一种常见的消遣活动(Billieux等人,2017; Griffiths等,2017)。 此外,电子游戏一直是公众辩论的中心,关于他们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但是 游戏紊乱 在诊断手册中增加了父母和公众对过度游戏的担忧(弗格森,2010).
在他们的精神障碍诊断手册的最新版本中,DSM-5,(美国精神病学协会,2013合并 互联网游戏障碍 (IGD)在其附录中作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条件。 根据DSM-5的定义,IGD的临床诊断应该以连续使用互联网视频游戏为特征,这些视频游戏会在个人,社交,学术和工作中产生重大问题。 在1年内满足这九个诊断标准中的五个表明存在这种疾病:(a)渴望,(b)戒断,(c)耐受,(d)复发,(e)失去兴趣,(f)持续尽管存在问题意识,(g)欺骗,(h)情绪调整,以及(i)危及工作/教育/关系。 然而,已经确定了对这些诊断标准的若干限制,包括在游戏成瘾术语中使用术语“互联网”,其排除了在线和离线都可能发生游戏成瘾的选项(Király等人,2015; Kuss等人,2017)。 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第一步之后,世界卫生组织(WHO)现已决定将修订后的诊断纳入其中 游戏紊乱 (GD)在他们的诊断手册ICD-11中。 一些研究认为GD是一种与几种心理并发症相关的全球性问题(Kuss和Griffiths,2012)。 睡眠质量差,失眠,工作或学业表现下降,认知能力下降,人际关系困难,负面影响增加,压力,攻击性和敌意只是对受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的一些严重后果由GD(Kuss和Griffiths,2012).
然而,之前的研究一再表明,该领域的主要障碍严重阻碍了研究进展,大多数研究从非临床和规范性社区样本中得出了他们的发现(Kuss等人,2017)。 因此,对GD临床研究的兴趣正在增长,并且已经对临床人群进行了一些研究。 然而,由于缺乏GD临床人群的标准化程序,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对临床方法和程序做出了决定,其结果是使用异构方法和程序,可能会在新兴领域造成更多混乱和混乱(Kuss等人,2017)。 此外,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和共识,可能导致对假阳性增加的结果高估问题,但相反的风险是不承认并且不能充分治疗需要临床护理的人(Billieux等人,2017; Griffiths等,2017)。 因此,系统评价过程对于理解临床医生之间共享的临床实践以及进一步研究可包含在官方GD指南中的过程至关重要。 若干研究报告说,调整现有准则可以减少由于持续制定新准则而造成的可避免的重复工作(Baker和Feder,1997; Fervers等,2006)。 已经进行了许多临床研究的系统评价(King和Delfabbro,2014; Kuss和Lopez-Fernandez,2016; King等人,2017; Zajac等,2017但是,这些系统评价侧重于那些被诊断患有GD和/或评估培训和干预的患者的特征,而没有提供有关临床过程的信息。
事实上,大多数先前的系统评价将搜索范围限制在包括治疗结果的研究中(King和Delfabbro,2014; King等人,2017; Zajac等,2017),因此没有提供包含在其中的临床样本特征的完整和详尽的总结,并且这些研究的目的不是验证报告的治疗结果。 检查这些研究与理解用于诊断患有游戏成瘾的个体的诊断标准和诊断过程相关。 根据最近的研究(Király等人,2015; Kuss等人,2017),对GD的研究需要阐明临床背景中使用的诊断和临床过程。 此外,为了在GD的诊断过程中获得强有力的共识,必须确定和深化科学文献中报道的当前使用的临床程序。 因此,有必要进行系统评价,以便确定共同的临床实践,同时可以研究和深化差异和创新。 出于这个原因,还包括未评估治疗结果的临床研究对于对目前使用的程序进行最全面的描述非常重要,而不会忽略专业人员当前使用的诊断过程的重要信息。
最后,大多数关于临床诊断个体的游戏成瘾评论仅关注含有定量数据的研究(King和Delfabbro,2014; King等人,2017; Zajac等,2017)。 尽管这些限制性纳入标准允许加强理解GD的方法学方法,但它排除了包括定性研究和病例报告的机会,这些研究和病例报告可提供有关GD患者临床经验的相关信息。 鉴于需要就GD的诊断方面确定共识(即诊断标准,诊断程序,所涉及的工作人员,治疗类型和治疗结构),必须涵盖已评估其特征的研究。临床病人。 在建立官方诊断阶段,排除定性研究,单个病例和病例报告可能会导致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产生差距。 本综述旨在通过考虑临床背景,诊断标准,诊断程序,所涉及的从业人员以及所应用的相应治疗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填补知识空白。 回顾GD患者使用的仪器,诊断标准和整个诊断过程(包括相关人员)可以综合当前的评估和诊断实践,并有助于建立GD诊断的一致共识,同时识别GD诊断的差异。 同样,对治疗和治疗结构类型的系统评价可以确定GD目前的干预方式,以帮助为从业者确定实用指南和说明。 此外,本次审查将审查文化背景和进行临床研究的国家。 这方面是相关的,因为不同文化的患病率特别多样(Kuss等人,2014并且还因为文化背景可以基于社会规范,共同信仰和共同实践为游戏活动赋予意义(Kuss,2013).
目的
总之,本系统评价旨在为GD患者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的当前诊断程序和干预提供广泛的跨文化图景。 因此,我们审查了包括博弈患者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检查用于诊断和治疗GD患者的临床程序,包括文化背景和进行研究的国家,用于测量GD的工具,诊断标准,使用的诊断程序(包括所涉及的工作人员)和应用的治疗方案。
付款方式
协议,注册和资格标准
本系统评价侧重于临床诊断为GD的个体,并基于描述临床实践中使用的诊断或干预程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PRISMA报告系统评价的声明获得通过(Liberati等,2009),该协议以前未在此次审核中注册。 纳入标准由两位作者就编码过程达成一致意见编码,并且:(a)包括临床样本和/或游戏成瘾的临床干预; (b)包含定量和/或定性数据; (c)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 (d)以下列语言之一(作者的口头语言)提供全文:英语,德语,波兰语和意大利语。
信息来源和搜索策略
通过在2月至4月2018中搜索学术数据库Scopus,WoS,PubMed,PsycINFO和psycARTICLES来确定现有论文。 没有使用过滤年份的过滤器。 两位作者都为系统搜索定义了一个商定的英语关键词列表,该列表分为两类词(及其衍生词)。 第一组包含以下词语:游戏*成瘾; 游戏成瘾; 游戏*混乱; 游戏障碍; 游戏*依赖; 游戏依赖; 强制*游戏*; 强制游戏; 病态*游戏*; 病理性的*游戏; 过度游戏*; 过度游戏; 有问题的游戏*; 有问题的游戏。 第二组词包含以下词语:门诊*; DIAGNOS *; 对待*; therap *; 患者*; psychotherap *; 军医*; 培养*; 法律顾问*; intervent *; EDUC *; Psychoeduc *。
研究选择和数据收集过程
PsycInfo上的第一次搜索显示了106论文,第二次搜索WOS发现了181论文,Scopus搜索发现了181论文,PUBMED 13论文被发现,而4论文则是通过搜索psyARTICLES得到的。 第二步,重复的论文被排除在外,为了广泛报道,使用Google学术搜索和其他论文的参考列表进行了搜索,增加了三篇论文。 系统评价的论文选择基于前面描述的纳入和排除标准。 遵循流程图中提供的搜索策略 图1对文章标题和摘要的检查最后总结了28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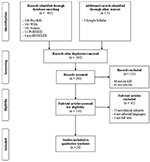 图1。 符合PRISMA指南的流程图(Liberati等,2009).
图1。 符合PRISMA指南的流程图(Liberati等,2009).数据项,偏差风险和结果综合
从研究中获得与文化背景,用于测量GD的仪器,诊断标准,进行的诊断程序以及所采用的治疗方案有关的数据。 考虑到该系统评价的探索性,并且对GD患者临床环境中当前应用的程序有广泛的了解,因此并未根据研究质量对研究进行过滤,而是将定性和定量研究都考虑在内。 此外,根据PRISMA指南评估了研究中偏倚风险的总体概况。 每项研究均使用Cochrane协作工具(希金斯和格林,2011)用于评估以下偏见的风险:选择偏差(描述干预措施或群体的分配质量); 绩效偏差(描述各组间干预或评估过程中使用的程序的质量); 检测偏差(描述结果确定中程序的质量); 流失偏见(描述管理遗失,撤回和不完整数据的程序质量); 报告偏差(描述报告结果和结果的程序质量)。 报告了一种或多种偏见风险 补充表1.
鉴于研究方法中各研究数据的高度异质性,未进行荟萃分析,数据通过汇总表和使用这些类别的叙述综合进行定性合成:(1)该国的文化背景进行研究的地方; (2)用于测量GD的仪器; (3)GD的诊断标准; (4)使用的诊断程序; 和(5)应用的治疗方案。
成果
研究选择与特征
在本次审查中,通过在科学数据库中搜索关键字来确定第一组485论文。 如流程图所述,225论文被排除,因为它们是复制记录,88论文被排除,因为主题不是GD,65记录被排除,因为它们是诉讼摘要或书评(不是科学同行评审论文),73论文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有描述GD的临床患者,6论文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是用作者没有说的语言写的,有三篇论文因为没有全文而被排除在外。 共有28研究符合纳入标准,这些研究列于 补充表1。 出版日期范围从2010到2018,并包含诊断为GD的临床样本。
研究中的偏见风险
一些研究(张等人,2016a,b, 2018; 邓等人,2017; King等人,2018)被认为有选择偏倚的风险,因为实验组或对照组的分配不是随机的,或者因为实验组仅由同意参加临床社区的患者组成。 在所有研究中,不可能估计性能偏差,因为参与者和人员的盲法程序无法应用,因为只有一个组接受了干预(例如,临床组与健康组)。 一项研究也报告了检测偏倚的风险(Eickhoff等,2015)因为结果完全基于进行干预的同一治疗师的报告。 一些研究(Eickhoff等,2015; van Rooij等人,2017; 张等人,2016a,b, 2018; King等人,2018)由于干预数据不完整,或者检测到大量缺失或不完整的数据,因此可能存在消耗偏差的风险。 一些研究(Eickhoff等,2015; Park等,2016b, 2017; Vasiliu和Vasile,2017)显示报告偏差,因为没有报告关于结果和治疗评估的所有信息,或者因为没有报告影响大小。
结果综合
本次审查的重点是:(1)国家进行的研究和文化背景的审查; (2)用于测量GD的仪器; (3)GD的诊断标准; (4)进行的诊断程序; 和(5)应用的治疗方案。
文化背景
从纳入研究的分析中,出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 尽管该评价仅基于28论文,但结果显示大多数研究是在亚洲大陆进行的,韩国是12研究中代表性最高的国家。 在中国进行了五项研究,两项在台湾进行,一项在日本进行。 在欧洲国家进行了五项研究,其中两项在西班牙进行,其余单项研究在德国,荷兰和挪威进行。 最后,分别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了一项研究。 在一项研究中(Vasiliu和Vasile,2017),进行研究的国家尚未明确报告。 总的来说,结果显示,在亚洲大陆进行的临床试验次数最多,韩国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 其他国家的临床研究数量相当少。 GD的文化代表性似乎存在很大差异,表明需要从跨文化的角度进一步研究GD。
多维数据监测
在本评价纳入的研究中,GD用不同的仪器进行测量。 大多数研究(n = 16)使用GD的非特定测量,但是网络成瘾的一般测量。 十一项研究(Han等人,2010, 2012a,b; Han和Renshaw,2012; Kim等人,2012, 2015; Park等,2016a,b, 2017; Lee等人,2017; Nam et al。,2017)使用了杨氏互联网成瘾测试(IAT; 年轻,1996),而六项研究则使用了Chen的互联网成瘾量表(CIAS; 陈等人,2003)。 IAT是一个20项目问卷,它使用几个截止点来区分互联网用户。 九项研究(Han等人,2010, 2012a,b; Han和Renshaw,2012; Kim等人,2012; Park等,2016a,b; Lee等人,2017; Nam et al。,2017使用了50的截止, Kim等人。 (2015) 在研究中使用了70的截止值 Park等。 (2017),没有报告截止。 陈的互联网成瘾量表(CIAS; 陈等人,2003)是26项目的自我报告指标,包括互联网使用相关症状的五个维度(强迫使用,退出,容忍,人际关系问题和生活管理)。 四项研究(张等人,2016a,b, 2018; 邓等人,2017本评论中包含的CIAS使用了67的截止值来进行有问题的使用 Ko等人。 (2014) 和 姚等人。 (2017) 没有报告截止日期。 所有其他研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评估GD。 Müller等人。 (2014) 使用13项目自我报告量表评估互联网和电脑游戏成瘾(AICA-S; Wölfling等,2011)来自成瘾障碍的标准,并允许GD行为分类为正常(0-6.5点),中度上瘾(7-13点)和严重上瘾使用(≥13.5点)。 Pallesen等。 (2015) 使用了青少年游戏成瘾量表(GASA; Lemmens等,2009)包含21项目评级的5项目,其中涉及成瘾的七个维度(突出,容忍,情绪修改,退出,复发,冲突和问题),以及问题视频游戏比赛(PVGPS; Tejeiro Salguero和Morán,2002)由九个二分项组成。 使用的截止日期 Pallesen等。 (2015) 青少年游戏成瘾量表(GASA;等于或高于3分); Lemmens等,2009). Torres-Rodríguez等人。 (2017) 使用了与视频游戏相关的体验问卷(CERV; Chamarro Lusar等人,2014),以及互联网游戏紊乱测试(IGD-20测试; Pontes等,2014)。 视频游戏相关经验问卷(CERV; Chamarro Lusar等人,2014)是一个17项4点Likert量表并使用等于或高于39的截止值,而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Test(IGD-20 Test; Pontes等,2014)是20项Likert量表的5项自我报告量表,截止值高于或等于71。 van Rooij等。 (2017) 使用临床视频游戏成瘾测试(C-VAT 2.0)和视频游戏成瘾测试(增值税; van Rooij等人,2012)。 临床视频游戏成瘾测试(C-VAT 2.0)包含三个关于游戏的问题,以及基于XDUMX DSM-11 IGD标准的过去一年GD行为的9二分问题。 视频游戏成瘾测试(增值税; van Rooij等人,2012)是一个14项目的自我报告量表,可以衡量各种有问题的游戏行为的严重程度(例如,失去控制,冲突,专注/突出,应对/情绪调整和戒断症状)。
Vasiliu和Vasile(2017) 使用互联网游戏障碍量表 - 简表(IGDS-SF; Sarda等人,2016)包含基于DSM-9标准的5项自我报告,该标准在6点范围内评定,范围从1(根本不是)到6(完全)。 金等人。 (2018) 使用了互联网游戏紊乱清单(IGD清单;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2013)包括以二分法(是/否)评定的9项目自我报告指标,以根据DSM-5 IGD分类评估IGD症状(专注,容忍,退出,不成功限制游戏,欺骗或关于游戏的谎言,对其他活动失去兴趣,尽管知道伤害,使用逃避或减轻负面情绪,以及伤害。 金等人。 (2018) 还包括互联网博彩提款量表(IGWS; Flannery等,1999)在他们的研究中,衡量游戏思想的频率和持续时间,最强烈的游戏渴望强度,抵抗游戏的能力以及渴望的整体力量。 最后,三项研究(Mallorquí-Bagué等,2017; Sakuma等,2017; Yeh等人,2017)使用半结构化临床访谈,将9个提议的DSM-5标准作为指南,并至少截止5或更多标准。 Sakuma等。 (2017) 还使用格里菲斯的成瘾的六个组成部分作为半结构化临床访谈的指南(格里菲斯,2005).
尽管该综述仅基于28项研究,但总体而言,在临床领域中,评估GD的工具的异构性和多样性非常高。 尽管使用的工具之间的差异还归因于撰写和进行研究的不同时间段,但是评估过程也发生了变化(即DSM-5发布之前和之后),这也表明迄今为止,尚未确定用于测量GD的标准和共同标准,并且尚未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 用于诊断的一些工具基于在互联网上花费的时间,而其他工具则基于DSM-5中APA对IGD进行分类的症状,或针对物质滥用/依赖性和病理的DSM IV-TR标准赌博。 在临床评估方面的这些差异削弱了整个研究中流行率和发生率的分析和比较。
诊断过程
在研究中使用将临床样品中的受试者包括的不同程序和方法。 大多数研究(Han等人,2010, 2012a,b; Han和Renshaw,2012; Kim等人,2012, 2015; Müller等人,2014; Park等,2016a,b; van Rooij等人,2017; Lee等人,2017; Mallorquí-Bagué等,2017; Sakuma等,2017; Torres-Rodríguez等人,2017)从之前评估过GD患者的临床中心或医疗部门招募他们的样本,因此没有报告关于诊断过程的大量信息。 但是,这些研究中有9项(Han等人,2010, 2012a,b; Han和Renshaw,2012; Kim等人,2012, 2015; Park等,2016a,b; Lee等人,2017)还使用DSM-IV结构化临床访谈的初步筛选来评估纳入和排除标准。 两项研究(van Rooij等人,2017; Mallorquí-Bagué等,2017)根据DSM-V标准进行任何DSM-IV轴诊断的扩展,同时进行四项研究(Müller等人,2014; Park等,2017; Sakuma等,2017; Torres-Rodríguez等人,2017)使用外部专家评级(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执行)根据DSM-5定义纳入标准。
六项研究(Pallesen等人,2015; 张等人,2016a,b, 2018; 邓等人,2017)报告通过在线问卷调查,报纸广告和电话筛选选择参与者,并使用面对面的半结构化筛选来评估诊断标准的满足程度。 然而,尽管所描述的治疗是由治疗师和心理学家进行的,但诊断人员和程序没有详细描述。 同样的, 金等人。 (2018) 筛选出具有临床定义的游戏问题的成年人,他们自愿访问了提供退出或减少游戏资源的网站。 心理测量仪器结合开放式后续问题,可以检查参与者是否符合五个或更多DSM-5 IGD标准,并亲自承认他们的游戏问题。
四项研究(Han和Renshaw,2012; Ko等人,2014; 姚等人,2017; Yeh等人,2017通过广告招募参与者,在对一些诊断标准进行初步评估后,由精神科医生进行访谈以确定IGD的诊断。 参与者的研究 Nam等人。 (2017) 在与精神科医生进行临床访谈后被诊断出来。 艾克霍夫等人。 (2015) 描述了在经历了几种干扰其工作活动的症状后,通过军事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接受GD诊断的三名军人的案例。 军事人员在会议期间单独诊断出三名军人。 Vasiliu和Vasile(2017) 进行了精神病学访谈以做出诊断。 Kim等人。 (2013) 没有报告在他们的研究中进行的诊断过程,而只报告他们使用的诊断标准。
许多研究报告包括有关整个诊断过程的有限信息,这是未来临床研究应该克服的限制。 虽然该评价仅基于28研究,但是,大多数研究包括由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进行的访谈。 尽管就诊断过程中涉及的专业人员的使用达成了一致意见,但访谈内容和结构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
诊断标准
该评价的研究表明,标准的组合通常用于诊断GD。 大多数研究(Han等人,2010, 2012a,b; Han和Renshaw,2012; Kim等人,2012, 2013, 2015; Ko等人,2014; Park等,2016a,b; 张等人,2016a,b, 2018; 邓等人,2017; Lee等人,2017; Nam et al。,2017; Vasiliu和Vasile,2017; 姚等人,2017; Yeh等人,2017)报告游戏时间作为诊断标准,具有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一个:(a)高于或等于每天2和4 h之间的范围; (b)周末每天的8小时或更长的游戏时间; (c)每周14和40 h之间。 此外,一些研究(Han等人,2010, 2012b; 邓等人,2017; Yeh等人,2017)还定义了维持互联网游戏模式的最短时间,范围在1和2年之间。
大多数研究还使用DSM-IV标准进行药物滥用(Han等人,2010; Han和Renshaw,2012; Kim等人,2012, 2013, 2015; Park等,2016a,b; Lee等人,2017; Nam et al。,2017),专注于视频游戏中受损行为或遇险。 十项研究(Ko等人,2014; Müller等人,2014; Eickhoff等,2015; van Rooij等人,2017; 邓等人,2017; Mallorquí-Bagué等,2017; Park等,2017; Sakuma等,2017; Torres-Rodríguez等人,2017; 姚等人,2017; Yeh等人,2017; King等人,2018据报道,IGD的诊断是通过支持九个DSM标准中的至少五个或更多来确定的(对游戏的过度使用或关注;戒断症状;容忍;未能停止或减少游戏;对其他活动失去兴趣;继续尽管有消极的后果,但要使用互联网游戏的数量;用于逃避或减轻负面情绪的游戏;以及人际关系,工作或教育的损害)。
一些研究还报告了评估的特定IGD症状。 艾克霍夫等人。 (2015) 据报道,由于游戏,工作表现不佳,失眠,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烦躁不安和情绪低落。 四项研究(Han等人,2010, 2012b; Han和Renshaw,2012; Kim等人,2012)描述了受试者报告持续期望玩互联网游戏和未能减少游戏。 此外,据报道,工作或学业表现下降,人际关系受损,日常生活中断和昼夜节律受到干扰。 当有人要求他们停止游戏时,也会报告负面情绪和/或反对行为。 Kim等人。 (2013) 据报道,患者倾向于报告学业状况,社交恐怖症和/或昏睡行为的急剧下降。 Torres-Rodríguez等人。 (2017) 据报道,有四种令人上瘾的病例,当他们无法玩耍时变得烦躁,放弃了自己的爱好,不再与朋友互动,家庭冲突加剧,学习成绩下降,渴望玩电子游戏,心理依赖,以及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van Rooij等。 (2017) 据报道,参与者将所有空闲时间甚至部分学校时间用于游戏。 此外,大多数患者存在家庭问题,社交圈受到干扰,学校表现下降。 Vasiliu和Vasile(2017) 据报道,一项患者的案例研究逐渐增加了游戏活动的日常工作时间,带来了负面的学术后果,失去了对游戏相关活动的控制感,忽视了他在房子周围的职责和他的社交关系(与女友分开,并失去了他的大多数非游戏朋友)。
纳入研究最受关注的标准是临床上显着的损害(即危及工作/教育/关系,行为受损)。 这可能是因为当游戏体验在日常生活中引起重大影响时,会出现对专业支持的请求。 除了这个特定的标准,本评价中包含的研究使用不同的诊断GD的标准。 一些研究使用DSM IV-TR标准进行药物滥用,其他研究使用DSM-5中的IGD标准,一些研究主要根据专用于游戏的时间进行诊断。 当然,这种差异也可能归因于文章进行和发布的不同时期。 虽然在本次审查中无法评估出版时间与诊断方案之间的关系,但在2015之后发表了9篇论文(Kim等人,2015; Park等,2016a,b; 张等人,2016a,b, 2018; 邓等人,2017; Lee等人,2017; Nam et al。,2017),并报告一般互联网成瘾工具的互联网使用和/或分数作为诊断标准。 对临床患者的研究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已经进行或开始研究时发生变化是正常的。 不幸的是,只有少数研究表明临床受试者必须满足哪些诊断标准才能做出诊断,从而削弱以确定GD诊断标准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疗程
18项研究对GD进行了治疗,其中大部分(Han等人,2010; Han和Renshaw,2012; Kim等人,2012, 2013; Eickhoff等,2015; Pallesen等人,2015; Nam et al。,2017; Park等,2017; Torres-Rodríguez等人,2017; Vasiliu和Vasile,2017除了七项研究外,还采用了一种适用于门诊患者的个体化方法(Park等,2016b; 张等人,2016a,b, 2018; 邓等人,2017; Sakuma等,2017; 姚等人,2017)使用团体治疗方法,和(Han等人,2012a)使用家庭疗法。
通过心理教育培训,睡眠卫生和虚拟现实治疗,各种方法在方法和方面各不相同(Kim等人,2013; Eickhoff等,2015; Park等,2016b; Torres-Rodríguez等人,2017)。 通常,最常用的方法是用于个体治疗的认知行为疗法(CBT)(Kim等人,2012; Pallesen等人,2015; Torres-Rodríguez等人,2017; Vasiliu和Vasile,2017), 姚等人。 (2017) 和 Park等。 (2016b) 使用了一组行为干预。 CBT通常从8到10会话,每个会话持续在1和2之间。 渴求行为干预(CBI)是最常用的群体治疗,包括2.5-3 h组织的几个主题会议:(1)热身运动,(2)关于上一次会议的家庭作业的讨论,(3)a主要结构化活动,(4)简要概述,(5)和家庭作业。 五项研究使用药物治疗干预。 这些主要基于安非他酮缓释(SR)治疗(Han等人,2010; Han和Renshaw,2012; Kim等人,2012; Nam et al。,2017),而 Park等。 (2017) 使用药物治疗与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所有使用治疗的18研究都报告了GD的症状减轻和/或游戏的频率,以验证治疗效果。 其中六项研究(Han和Renshaw,2012; Kim等人,2012; Nam et al。,2017; Sakuma等,2017; 姚等人,2017; Yeh等人,2017)还研究了心理健康指标,如抑郁,冲动,焦虑,自尊和生活满意度。 此外,在五项研究中(Han等人,2010; Park等,2016b; 张等人,2016a,b, 2018)通过fMRI评估神经心理学变化。 韩等人。 (2012a) 也显示出感知家庭凝聚力的改善 Kim等人。 (2013) 表现出写作和口语能力的提高。 一般而言,所有经过审查的研究都表明,干预措施可以改善GD患者,强调需要采取干预措施来帮助解决与游戏功能失调相关的问题体验(Griffiths等,2017).
总之,结果显示临床研究主要使用CBT干预和心理药物疗法。 然而,案例研究和临床报告的纳入突出了其他类型的干预措施,如心理教育培训,睡眠卫生和虚拟现实治疗,目前在临床实践中使用。 这表明,检查常用的治疗方法以创建和验证可靠有效的指南可能也是有用的。
讨论
自从5中发布了DSM-2013 IGD诊断标准以来,已经发现缺乏临床研究是全面了解GD现象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Griffiths等,2016)。 出于这个原因,本评价的目的是确定和模式化使用被诊断患有GD的受试者的研究结果。 为了尝试全面了解目前在各个国家使用的临床实践,有必要包括在线和离线使用GD临床样本的定性和定量研究,这些研究不仅限于包括治疗结果的研究。 这项研究的结果导致了28研究的鉴定,这些研究根据以下方面进行了深化和分类:(a)进行研究的文化背景; (b)广东省的措施; (c)诊断的诊断标准; (d)适用的诊断程序; (e)适用的最终治疗方案。
证据总结
在文化背景方面,结果清楚地表明,大多数研究都是在亚洲大陆进行的(20对28的总体研究),其中一半以上是在韩国进行的。 这证实了以前使用临床样本的考虑因素Király等人,2015; Kuss和Lopez-Fernandez,2016)报告了韩国技术成瘾政策的进展情况,该政策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心和大型项目来处理从2002开始的问题,而在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甚至没有涵盖GD处理通过国家卫生基金。
关于用于评估GD的工具,最突出的最矛盾的方面是尽管进行了审查(King等人,2013)确定了18用于评估GD症状的特定工具,大多数临床患者的研究倾向于使用一般的网络成瘾工具,如IAT(年轻,1996)和CIAS(陈等人,2003)。 自然地,这种差异是由于临床患者的研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出结论和发表,因此现在可用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现在可能过时的措施和标准,但这些措施和标准很常见,广泛用于研究的计划和开始阶段。 事实上,使用一般的网络成瘾工具可能是倾向于将GD视为网络成瘾的子域。 这个愿景源于GD的早期概念化(庞特和格里菲斯,2014),已经被DSM-5放大了使用“互联网”术语来定义GD标准。 尽管存在这种矛盾,但很明显,在诊断过程中使用GD特定工具的研究如何增加,包括以下工具:AICA-S(Wölfling等,2011),GASA(Lemmens等,2009),PVGPS(Tejeiro Salguero和Morán,2002),CERV(Chamarro Lusar等人,2014),IGD-20测试(Pontes等,2014),增值税(van Rooij等人,2012)和IGDS-SF(Sarda等人,2016)。 然而,风险依然存在,如此庞大且不同数量的工具无助于确定和验证通用的评估标准。 关于测量问题向前迈进了一步 van Rooij等。 (2017),他们对C-VAT 2.0进行了临床验证,使用临床样本测试敏感性并改善对诊断为GD的患者的正确鉴定。 虽然所有上述仪器都显示出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例如可靠性和结构有效性,但只有C-VAT 2.0报告了良好的临床有效性。
就诊断过程而言,很难全面了解受试者的诊断情况,因为大多数患者在临床中心被独立诊断,然后被招募用于研究目的,而不是通过研究团队跟踪研究团队。整个诊断过程。 尽管存在这种限制,但可以得出关于这些临床研究中使用的程序的几个有趣结论。 大多数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特征是,与专业人士(如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进行面谈(具有不同的结构水平)或对多学科人员进行评估有助于诊断。 在许多研究中,这种访谈具有评估包含和排除相应研究的参与者标准的功能,并且可以被认为是完整评估的良好实践(美国精神病学协会,2013)。 需要记住的一个方面是,许多研究经常在评估中使用DSM-IV-R的诊断标准,并且仅在某些情况下将它们更新为DSM-5标准。 这种异常来自于在DSM-5标准发布之前已在干预中心内诊断出的研究中包括的患者,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临床样本的研究在新诊断手册出版之前公布。 这方面进一步强调,有必要对临床样本进行更频繁的检查,以巩固新的诊断标准,并建立评估和诊断GD的独特标准(Kuss和Lopez-Fernandez,2016; Kuss等人,2017).
与前一点相关,DSM IV-TR物质滥用/依赖标准通常用于定义GD(容忍,退出,预期效果,失控,游戏花费的时间过长,尽管存在问题仍然存在,并减少其他活动) 。 使用DSM-5标准来定义诊断的研究仍然较少(本评价中有10项):(a)渴望,(b)戒断,(c)耐受,(d)复发,(e)丧失兴趣,(f)尽管存在问题仍在继续,(g)欺骗,(h)情绪调整,以及(i)危害工作/教育/关系。 除了DSM标准之外,大多数研究还使用了受损行为或窘迫的存在,因为视频游戏是诊断因素,并且使用这些特定截止值的视频游戏的频率很高:(a)大于或等于范围每天2和4之间; (b)周末每天的8小时或更长的游戏时间; (c)每周游戏的14和40之间。 一些案例研究还显示,诊断为GD的患者出现以下症状:学校或工作表现恶化,负面情绪,人际关系受损,放弃爱好,日常生活和昼夜节律中断,负面情绪或反对行为等因素停止播放的请求,以及失去对游戏相关活动的控制感。 最后,所提出的研究经常引用戒断和耐受症状,迄今为止尚未达成完全科学协议(Király等人,2015)。 因此,发布时间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事实上,大多数所描述的研究都是在DSM-5标准尚不可用时定义和实施的。 有理由期待GD的诊断和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准确和有效。 但是,如果此时可以观察到过去使用过程的相当大的异构性,随着DSM-5和ICD-11的发布,将来可能存在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更加分散。
很明显,在临床实践中,DSM的指导方针始终指导诊断和治疗。 如果在过去GD诊断是通过适应物质依赖标准来指导的,那么在DSM-5中包含IGD肯定是分享特定标准的重要的第一步。 然而,从结果分析中,似乎很清楚诊断标准需要在临床环境中进行验证。 目前,不可能将病理行为与非病理行为明确区分开来。 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用游戏所花费的时间量的标准来表示。 虽然本评价中的大多数研究都使用这一标准来诊断GD,但之前的研究表明,专业游戏玩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游戏(Faust等人,2013),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发展成瘾(Kuss等人,2012)。 在这篇综述中,无法分析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在诊断背景下所面临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的信息。 然而,未来的研究应该深化这一过程,因为识别敏感和特定的诊断过程以及准确的截止点至关重要。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是诊断标准在时间和背景方面的可靠性。 为了具有有效的诊断过程,如果在短时间之后重复,或者当由不同的个体(例如,不同的专业人员)或在不同的环境(例如,不同的诊所)中重复时,诊断也是可靠的和相似的也是必要的。 目前,仪器,诊断标准和临界值的异质性使得诊断程序不清楚。 因此,迫切需要旨在验证GD标准的研究。
最后,本系统评价中描述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治疗程序。 结果证实了之前对IA和GD治疗研究的评论(King和Delfabbro,2014; Kuss和Lopez-Fernandez,2016; King等人,2017; Zajac等,2017),表明最常用的治疗形式是CBT(及其变异)和精神药物治疗。 该系统评价中出现的一个相关方面是,临床实践中也可以使用研究报告中通常描述的不同方法。 一些研究(Kim等人,2013; Eickhoff等,2015; Park等,2016b)用作个人或团体治疗:心理教育培训,睡眠卫生和虚拟现实治疗。 睡眠卫生被发现是一种有助于GD症状管理的程序,因为发现延长的夜间游戏会危害工作表现和健康。 睡眠卫生包括不同的做法,以帮助患者获得良好的睡眠习惯。 此外,虚拟现实治疗(VRT)是一种使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心理治疗方法,包括三个步骤:放松,模拟高风险情况和声音辅助认知重组,导致GD严重程度的重要降低。 最后, Kim等人。 (2013) 报道了GD的学生如何从使用从游戏借来的叙述方面的写作和口语教育培训中受益。 这些类型的干预通常不在先前的系统评价中提出,并且通常不被描述为GD的典型训练技术。 出于这个原因,有必要打电话,以更广泛地传播世界各地的临床医生对GD患者进行的所有干预措施。 这将通过新的评论和荟萃分析扩大其扩散并验证其有效性。 在像GD一样的新领域,诊断和治疗过程仍在进行中,每天在诊所工作的人和验证治疗有效性的人之间的两条平行路径之间旅行的风险和进行研究必须避免。
限制
鉴于纳入研究的局限性,应考虑系统评价的结果。 第一个限制是未出版的材料未被包括在内。 对于更频繁地发表积极成果的趋势,这可能会产生发表偏见。 另一个相关的限制是,评论中仅添加了以某些语言发布的论文。 这可能会排除一些以非英语国家撰写的以本国语言报告结果的相关论文。 此外,该系统评价仅具有描述性和探索性目的,无法验证诊断过程和治疗质量。 未来的研究应尝试对临床研究进行更具体的评估,并应更多地关注GD的临床方面,以为从业者建立清晰和共享的指南。
含义和结论
从临床研究的回顾来看,在诊断和干预过程中,仪器的选择存在很大的异质性。 如果DSM-5标准的发布是GD领域的“地震”(Kuss等人,2017),IGD-11的出版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因此,有必要为可以指导临床实践并允许在该领域进行协作和发展的研究人员创建共同基础。 GD临床人群中标准程序的验证似乎是未来研究的必要优先事项。 关于政治影响,有必要制定与国家和国际委员会合作的协议,以便在世界各地建立治疗和预防中心,以加快GD患者管理指南的标准化进程。
作者贡献
SC生成了稿件的初稿,对文件进行了识别和检索,以纳入系统评价。 DK负责监督和协调整个工作,准备,编写和编辑手稿。
资金
这项研究得到了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心理学系的Kickstarter资助。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研究是在没有任何可被解释为潜在利益冲突的商业或金融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
补充材料
本文的补充材料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g.2019.00578/full#supplementary-material
表S1。 审查的研究摘要。
参考资料
Adair,CE,Marcoux,GC,Cram,BS,Ewashen,CJ,Chafe,J.,Cassin,SE,et al。 (2007)。 开发和多地点验证新的条件特定的生活质量衡量饮食失调。 健康质量 生活成果 5, 23–37. doi: 10.1186/1477-7525-5-23
Beck,AT,Epstein,N.,Brown,G。和Steer,RA(1988)。 用于测量临床焦虑的清单:心理测量属性。 J.咨询。 临床。 心理学。 56, 893–897. doi: 10.1037/0022-006X.56.6.893
Billieux,J.,King,DL,Higuchi,S.,Achab,S。,Bowden-Jones,H.,Hao,W。等。 (2017)。 功能障碍在游戏障碍的筛查和诊断中很重要:评述:关于世界卫生组织ICD-11游戏障碍提案的学者公开辩论论文(Aarseth等人)。 J. Behav。 冰火。 6,285-289。 doi:10.1556 / 2006.6.2017.036
Bush,K.,Kivlahan,DR,McDonell,MB,Fihn,SD和Bradley,KA(1998)。 AUDIT酒精消费问题(AUDIT-C):对饮酒问题进行有效的简短筛选测试。 拱。 实习生。 医学。 158,1789-1795。 doi:10.1001 / archinte.158.16.1789
Carver,CS和White,TL(1994)。 对即将到来的奖励和惩罚的行为抑制,行为激活和情感反应:BIS / BAS量表。 J. Pers。 SOC。 心理学。 67,319-333。 doi:10.1037 / 0022-3514.67.2.319
Chamarro Lusar,A.,Carbonell,X.,Manresa,JM,Munoz-Miralles,R.,Ortega-Gonzalez,R.,Lopez-Morron,MR,et al。 (2014)。 El Cuestionario de Experiencias Relacionadas con los Videojuegos(CERV):un instrumento para detectar el usoproblemáticodovideojuegos enadolescentesespañoles。 成瘾 26,303-311。 doi:10.20882 / adicciones.26.4
Chen,SH,Weng,LJ,Su,YJ,Wu,HM和Yang,PF(2003)。 中国网络成瘾量表的编制及其心理测量研究。 中国人J. Psychol。 45,279-294。 doi:10.1037 / t44491-000
Cox,LS,Tiffany,ST和Christen,AG(2001)。 在实验室和临床环境中评估吸烟催促(QSU-brief)的简要问卷。 尼古丁Tob。 RES。 3,7-16。 doi:10.1080 / 14622200020032051
De Freitas,S。和Griffiths,M。(2007)。 在线游戏作为学习和培训的教育工具。 BR。 J. Edu。 TECHNOL。 38,535-537。 doi:10.1111 / j.1467-8535.2007.00720.x
邓丽丽,刘丽娜,夏CC,蓝洁,张建堂,方XY(2017)。 对减轻大学生网络游戏障碍的渴望行为干预:一项纵向研究。 面前。 心理学。 8,526-538。 doi:10.3389 / fpsyg.2017.00526
DuPaul,GJ(1991)。 ADHD症状的家长和教师评级:基于社区的样本中的心理测量属性。 J. Clin。 儿童阿多尔。 心理学。 20, 245–253. doi: 10.1207/s15374424jccp2003_3
Eickhoff,E.,Yung,K.,Davis,DL,Bishop,F.,Klam,WP和Doan,AP(2015)。 在军事心理健康诊所接受治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过度使用电子游戏,睡眠不足以及工作表现不佳:案例系列。 米尔。 医学。 180,839-843。 doi:10.7205 / MILMED-D-14-00597
Faust,K.,Meyer,J。和Griffiths,MD(2013)。 竞争和专业游戏:讨论科学研究的潜在好处。 诠释。 J. Cyber Behav。 心理学。 学习。 3,67-77。 doi:10.4018 / ijcbpl.2013010106
Ferguson,C。(2010)。 炽天使还是生化危机? 暴力电子游戏可以成为一种好的力量吗? Rev. Gen. Psychol。 14,68-81。 doi:10.1037 / a0018941
Fervers,B.,Burgers,JS,Haugh,MC,Latreille,J.,Mlika-Cabanne,N.,Paquet,L.,et al。 (2006)。 适应临床指南:文献综述和框架和程序的建议。 诠释。 J. Qual。 卫生保健 18,167-176。 doi:10.1093 / intqhc / mzi108
Flannery,BA,Volpicelli,JR和Pettinati,HM(1999)。 宾夕法尼亚酒精渴望量表的心理测量属性。 醇。 临床。 进出口。 RES。 23, 1289–1295. doi: 10.1111/j.1530-0277.1999.tb04349.x
Forrest,CJ,King,DL和Delfabbro,PH(2017)。 适应不良的认知预测了高度参与的成年人中有问题的游戏的变化:12月的纵向研究。 冰火。 Behav。 65,125-130。 doi:10.1016 / j.addbeh.2016.10.013
Gearhardt,AN,Corbin,WR和Brownell,KD(2009)。 耶鲁食物成瘾量表的初步验证。 食欲 52,430-436。 doi:10.1016 / j.appet.2008.12.003
医学博士格里菲思(Griffiths),库斯(Dan Kuss),俄亥俄州的洛佩兹·费尔南德斯(Lopez-Fernandez)和密西西比州的庞特斯(2017)。 存在游戏问题,并且是游戏混乱的一个例子:评论:学者们就世界卫生组织ICD-11游戏障碍提案(Aarseth等人)进行公开辩论。 J. Behav。 冰火。 6,296-301。 doi:10.1556 / 2006.6.2017.037
Griffiths,MD,Van Rooij,AJ,Kardefelt-Winther,D.,Starcevic,V.,Király,O.,Pallesen,S.,et al。 (2016)。 努力就评估网络游戏障碍的标准达成国际共识:对Petry等人的批评性评论。 (2014)。 瘾 111,167-175。 doi:10.1111 / add.13057
Grüsser,S.,Hesselbarth,U.,Albrecht,U。和Mörsen,C。(2006)。 Berliner InventarzurGlücksspielsucht - 筛选器[柏林赌博筛选版本]。 研究报告。 柏林。
Hainey,T.,Connolly,TM,Boyle,EA,Wilson,A。和Razak,A。(2016)。 基于游戏的小学教育经验证据的系统文献综述。 COMPUT。 EDUC。 102,202-223。 doi:10.1016 / j.compedu.2016.09.001
Han,DH,Hwang,JW和Renshaw,PF(2010)。 安非他酮持续释放治疗减少了对网络视频游戏成瘾患者的视频游戏和线索诱导的大脑活动的渴望。 进出口。 临床。 精神药理学。 18,297-304。 doi:10.1037 / a0020023
Han,DH,Kim,SM,Lee,YS和Renshaw,PF(2012a)。 家庭治疗对在线游戏成瘾青少年在线游戏和大脑活动严重程度变化的影响。 精神病学 神经影像 202,126-131。 doi:10.1016 / j.pscychresns.2012.02.011
Han,DH,Lyoo,IK和Renshaw,PF(2012b)。 在线游戏成瘾和职业游戏玩家的差异区域灰质体积。 J. Psychiatr。 RES。 46,507-515。 doi:10.1016 / j.jpsychires.2012.01.004
Han,DH和Renshaw,PF(2012)。 安非他酮治疗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有问题的网络游戏。 J. Psychopharmacol。 26,689-696。 doi:10.1177 / 0269881111400647
Havenaar,JM,Van Os,J。和Wiersma,D。(2004)。 Algemene在de psychiatrische praktijk见面。 Tijdschr。 Psychiatr。 46,647-652。
Kim,H.,Kim,YK,Gwak,AR,Lim,JA,Lee,JY,Jung,HY,et al。 (2015)。 休息状态区域同质性作为网络游戏障碍患者的生物标志物:与酒精使用障碍和健康对照的患者进行比较。 PROG。 神经精神药理学。 生物学。 精神病学 60,104-111。 doi:10.1016 / j.pnpbp.2015.02.004
Kim,PW,Kim,SY,Shim,M.,Im,CH和Shon,YM(2013)。 教育课程对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玩家的语言表达和游戏成瘾处理的影响。 COMPUT。 EDUC。 63,208-217。 doi:10.1016 / j.compedu.2012.12.008
Kim,SM,Han,DH,Lee,YS和Renshaw,PF(2012)。 联合认知行为疗法和安非他酮治疗重症抑郁症青少年有问题的在线游戏。 COMPUT。 哼。 Behav。 28,1954-1959。 doi:10.1016 / j.chb.2012.05.015
Kim,YS,So,YK,Noh,JS,Choi,NK,Kim,SJ和Koh,YJ(2003)。 关于韩国ADHD评定量表(K-ARS)的父母和教师的规范数据。 J.韩国神经精神病学协会。 42,352-359。
King,DL,Adair,C.,Saunders,JB和Delfabbro,PH(2018)。 在寻求帮助的成年人有问题的游戏玩家中进行游戏禁欲的临床预测因素。 精神病学 261,581-588。 doi:10.1016 / j.psychres.2018.01.008
King,DL和Delfabbro,PH(2014)。 网络游戏障碍治疗:对诊断和治疗结果定义的回顾。 J. Clin。 心理学。 70,942-955。 doi:10.1002 / jclp.22097
King,DL,Delfabbro,PH,Wu,AMS,Doh,YY,Kuss,DJ,Pallesen,S.,et al。 (2017)。 网络游戏障碍的治疗:国际系统评价和CONSORT评估。 临床。 心理学。 启示录 54,123-133。 doi:10.1016 / j.cpr.2017.04.002
King,DL,Haagsma,MC,Delfabbro,PH,Gradisar,M。和Griffiths,MD(2013)。 走向病态视频游戏的共识定义:对心理测量评估工具的系统评价。 临床。 心理学。 启示录 33,331-342。 doi:10.1016 / j.cpr.2013.01.002
Király,O。,Griffiths,MD和Demetrovics,Z。(2015)。 网络游戏障碍和DSM-5:概念化,辩论和争议。 CURR。 冰火。 众议员。 2,254-262。 doi:10.1007 / s40429-015-0066-7
Kirby,KN,Petry,NM和Bickel,WK(1999)。 与非吸毒对照相比,海洛因成瘾者对延迟奖励的贴现率更高。 J. Exp。 心理学。 创 128,78-87。 doi:10.1037 / 0096-3445.128.1.78
Ko,C.-H.,Yen,J.-Y.,Chen,S.-H.,Wang,P.-W.,Chen,C.-S.,和Yen,C.-F。 (2014)。 台湾年轻人对DSM-5网络游戏障碍诊断标准的评估。 J. Psychiatr。 RES。 53,103-110。 doi:10.1016 / j.jpsychires.2014.02.008
Ko,CH,Hsiao,S.,Liu,GC,Yen,JY,Yang,MJ和Yen,CF(2010)。 网络成瘾大学生的决策特征,承担风险和个性。 精神病;。 175,121-125。 doi:10.1016 / j.psychres.2008.10.004
Kuss,DJ和Griffiths,MD(2012)。 网络游戏成瘾:对实证研究的系统评价。 诠释。 J. Ment。 健康瘾君子。 10, 278–296. doi: 10.1007/s11469-011-9318-5
Kuss,DJ,Griffiths,MD,Karila,L。和Billieux,J。(2014)。 网络成瘾:过去十年对流行病学研究的系统回顾。 CURR。 医药。 德。 20,4026-4052。 doi:10.2174 / 13816128113199990617
Kuss,DJ,Griffiths,MD和Pontes,HM(2017)。 DSM-5诊断网络游戏障碍的混乱和困惑:问题,担忧和建议,以便在该领域清晰。 J. Behav。 冰火。 6,103-109。 doi:10.1556 / 2006.5.2016.062
Kuss,DJ和Lopez-Fernandez,O。(2016)。 网络成瘾和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对临床研究的系统评价。 世界J.精神病学 6,143-176。 doi:10.5498 / wjp.v6.i1.143
Kuss,DJ,Louws,J。和Wiers,RW(2012)。 在线游戏成瘾? 动机预测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上瘾游戏行为。 Cyberpsychol。 Behav。 SOC。 网络。 15,480-485。 doi:10.1089 / cyber.2012.0034
Lee,YS,Son,JH,Park,JH,Kim,SM,Kee,BS和Han,DH(2017)。 网络游戏障碍患者与酒精依赖患者的气质和性格比较。 J.心理健康 26,242-247。 doi:10.1080 / 09638237.2016.1276530
Lejuez,CW,Read,JP,Kahler,CW,Richards,JB,Ramsey,SE,Stuart,GL,et al。 (2002)。 评估风险承担的行为测量:气球模拟风险任务(BART)。 J. Exp。 心理学。 申请 8, 75–84. doi: 10.1037/1076-898X.8.2.75
Lemmens,JS,Valkenburg,PM和Peter,J。(2009)。 开发和验证青少年的游戏成瘾量表。 媒体心理学。 12,77-95。 doi:10.1080 / 15213260802669458
Liberati,A.,Altman,DG,Tetzlaff,J.,Mulrow,C.,Gøtzsche,PC,Ioannidis,JP,et al。 (2009)。 PRISMA关于报告评估医疗干预措施的研究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的声明:解释和阐述。 PLoS Med 6:e1000100。 doi:10.1371 / journal.pmed.1000100
Lin,TK,Weng,CY,Wang,WC,Chen,CC,Lin,IM和Lin,CL(2008)。 健康台湾人的敌意特质和血管扩张功能。 J. Behav。 医学。 31, 517–524. doi: 10.1007/s10865-008-9177-0
Lovibond,PF和Lovibond,SH(1995)。 消极情绪状态的结构:抑郁焦虑应激量表(DASS)与贝克抑郁症和焦虑量表的比较。 Behav。 RES。 疗法。 33, 335–343. doi: 10.1016/0005-7967(94)00075-U
Mallorquí-Bagué,N.,Fernández-Aranda,F.,Lozano-Madrid,M.,Granero,R.,Mestre-Bach,G.,Baño,M.,et al。 (2017)。 网络游戏障碍和在线赌博障碍:临床和个性相关。 J. Behav。 冰火。 6,669-677。 doi:10.1556 / 2006.6.2017.078
Miller,WR和Tonigan,JS(1996)。 评估饮酒者的变革动力:变革准备阶段和治疗渴望度量表(SOCRATES)。 心理学。 冰火。 Behav。 10,81-89。 doi:10.1037 / 0893-164X.10.2.81
Moher,D.,Liberati,A.,Tetzlaff,J。和Altman,DGThe PRISMA,Group(2009)。 系统评价和元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PRISMA声明。 PLoS Med 6:e1000097。 doi:10.1371 / journal.pmed.1000097
Müller,KW,Beutel,ME,Egloff,B。和Wölfling,K。(2014)。 调查网络游戏障碍的风险因素:比较患有成瘾游戏,病态赌徒和健康控制的五大人格特征。 欧元。 冰火。 RES。 20,129-136。 doi:10.1159 / 000355832
Nam,B.,Bae,S.,Kim,SM,Hong,JS和Han,DH(2017)。 比较安非他酮和艾司西酞普兰对重度抑郁症患者过度网络游戏的影响。 临床。 精神药理学。 神经科学。 15,361-368。 doi:10.9758 / cpn.2017.15.4.361
Olson,DH(1986)。 Circumplex模型VII:验证研究和FACES III。 秘境。 处理。 25,337-351。 doi:10.1111 / j.1545-5300.1986.00337.x
Pallesen,S.,Lorvik,IM,Bu,EH和Molde,H。(2015)。 一项探索性研究,研究视频游戏成瘾治疗手册的效果。 心理学。 众议员。 117, 490–495. doi: 10.2466/02.PR0.117c14z9
Park,JH,Han,DH,Kim,BN,Cheong,JH和Lee,YS(2016a)。 有问题的网络游戏患者的社交焦虑,自尊,冲动和游戏类型之间的相关性。 精神病学调查。 13,297-304。 doi:10.4306 / pi.2016.13.3.297
Park,M.,Kim,YJ和Choi,JS(2017)。 网络游戏障碍患者持续不正常的信息处理:6月随访ERP研究。 药物 96,7995-8001。 doi:10.1097 / MD.0000000000007995
Park,SY,Kim,SM,Roh,S.,Soh,MA,Lee,SH,Kim,H.,et al。 (2016b)。 虚拟现实治疗程序对在线游戏成瘾的影响。 COMPUT。 方法程序Biomed。 129,99-108。 doi:10.1016 / j.cmpb.2016.01.015
Pontes,HM和Griffiths,MD(2014)。 网络成瘾和网络游戏障碍是不一样的。 J. Addict。 RES。 疗法。 5:e124. doi: 10.4172/2155-6105.1000e124
Pontes,HM,Király,O.,Demetrovics,Z。和Griffiths,MD(2014)。 DSM-5网络游戏障碍的概念化和测量:IGD-20测试的发展。 PLoS ONE的 9:e0110137。 doi:10.1371 / journal.pone.0110137
Radloff,LS(1977)。 CES-D量表:用于一般人群研究的自我报告抑郁量表。 申请 心理学。 MEAS。 1,385-401。 doi:10.1177 / 014662167700100306
Sakuma,H.,Mihara,S.,Nakayama,H.,Miura,K.,Kitayuguchi,T.,Maezono,M.,et al。 (2017)。 使用自我发现训练营(SDiC)治疗可改善网络游戏障碍。 冰火。 Behav。 64,357-362。 doi:10.1016 / j.addbeh.2016.06.013
Sarda,E.,Bègue,L.,Bry,C。和Gentile,D。(2016)。 网络游戏障碍和福祉:规模验证。 Cyberpsychol。 Behav。 SOC。 网络。 19,674-679。 doi:10.1089 / cyber.2016.0286
Sheehan,D.,Lecrubier,Y.,Sheehan,KH,Amorim,P.,Janavs,J。和Weiller,E。(1998)。 迷你国际神经精神病学(1998)。 迷你国际神经精神病学访谈(MINI):DSM-IV和CID-10的结构化诊断精神病学访谈的开发和验证。 J. Clin。 精神病学 59,22-33。
Tejeiro Salguero,RA和Morán,RMB(2002)。 测量问题视频游戏在青少年中播放。 瘾 97,1601-1606。 doi:10.1046 / j.1360-0443.2002.00218.x
Torres-Rodríguez,A.,Griffiths,MD,Carbonell,X.,Farriols-Hernando,N。和Torres-Jimenez,E。(2017)。 网络游戏障碍治疗:对四种不同类型的青少年问题游戏玩家的案例研究评估。 诠释。 J. Ment。 健康瘾君子。,1,1-12。 doi:10.1007 / s11469-017-9845-9
van Rooij,AJ,Schoenmakers,TM和van De Mheen,D.(2017年)。 C-VAT 2.0评估游戏障碍的工具的临床验证:对拟议的DSM-5标准和“视频游戏成瘾”年轻患者临床特征的敏感性分析。 冰火。 Behav。 64,269-274。 doi:10.1016 / j.addbeh.2015.10.018
van Rooij,AJ,Schoenmakers,TM,van den Eijnden,RJ,Vermulst,AA和van de Mheen,D。(2012)。 视频游戏成瘾测试:有效性和心理测量特征。 Cyberpsychol。 Behav。 SOC。 网络。 15,507-511。 doi:10.1089 / cyber.2012.0007
Vasiliu,O。和Vasile,D。(2017)。 网络游戏障碍和酒精使用障碍的认知 - 行为疗法 - 病例报告。 诠释。 J. Psychiatry Psychother。 2,34-38。 doi:10.1002 / cpp.2341
Wölfling,K.,Müller,KW和Beutel,M。(2011)。 Reliabilitätunductureitätderskala zum computerspielverhalten(CSV-S)。 PPMP-Psychotherapie·心身医学· Medizinische心理学。 61,216-224。 doi:10.1055 / s-0030-1263145
Yao,YW,Chen,PR,Chiang-shan,RL,Hare,TA,Li,S.,Zhang,JT,et al。 (2017)。 结合现实疗法和正念冥想减少了具有网络游戏障碍的年轻成人的跨期决策冲动。 COMPUT。 哼。 Behav。 68,210-216。 doi:10.1016 / j.chb.2016.11.038
Yeh,YC,Wang,PW,Huang,MF,Lin,PC,Chen,CS和Ko,CH(2017)。 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拖延:临床严重程度。 精神病学 254,258-262。 doi:10.1016 / j.psychres.2017.04.055
Young,KS(1996)。 计算机使用心理学:XL。 上瘾的互联网使用:一个打破刻板印象的案例。 心理学。 众议员。 79,899-902。 doi:10.2466 / pr0.1996.79.3.899
Zajac,K.,Ginley,MK,Chang,R。和Petry,NM(2017)。 网络游戏障碍和网络成瘾的治疗:系统评价。 心理学。 冰火。 Behav。 31,979-994。 doi:10.1037 / adb0000315
Zhang,JT,Ma,SS,Li,CR,Liu,L.,Xia,CC,Lan,J.,et al。 (2018)。 渴望对网络游戏障碍进行行为干预:修复腹侧纹状体的功能连接。 冰火。 生物学。 23,337-346。 doi:10.1111 / adb.12474
Zhang,JT,Yao,YW,Potenza,MN,Xia,CC,Lan,J.,Liu,L。,et al。 (2016a)。 渴望行为干预对网络游戏障碍中线索诱发渴望神经基质的影响。 NeuroImage Clin。 12,591-599。 doi:10.1016 / j.nicl.2016.09.004
关键词:游戏障碍,系统评价,临床研究,临床程序,诊断标准
引用:Costa S和Kuss DJ(2019)目前对游戏障碍的诊断程序和干预:系统评价。 面前。 心理学。 10:578。 doi:10.3389 / fpsyg.2019.00578
收到:17十二月2018; 接受:01 March 2019;
发布时间:27 March 2019。
编辑:
拉普森戈麦斯,澳大利亚联邦大学
点评人:
Claudio Imperatori,UniversitàEuropeadi Roma,意大利
Jose D. Perezgonzalez,新西兰梅西大学商学院
版权所有©2019 Costa和Kuss。 这是一份根据条款分发的开放获取文章 知识共享署名许可(CC BY)。 允许在其他论坛中使用,分发或复制,前提是原始作者和版权所有者被记入贷方,并且根据公认的学术惯例引用本期刊中的原始出版物。 不允许使用,分发或复制,不符合这些条款。
*通讯:Daria J. Kuss, [电子邮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