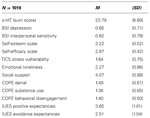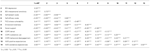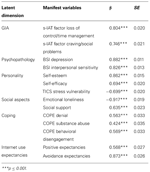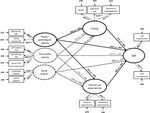面前。 Psychol。,11十一月2014 | doi:10.3389 / fpsyg.2014.01256
 马蒂亚斯·布兰德1,2 *,
马蒂亚斯·布兰德1,2 *,  Christian Laier1 和
Christian Laier1 和  金伯利S.杨3
金伯利S.杨3
- 1普通心理学系:认知,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德国杜伊斯堡
- 2Erwin L. Hahn德国埃森磁共振成像研究所
- 3互联网成瘾中心,Russell J. Jandoli圣文德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美国纽约Olean
网络成瘾(IA)已成为许多国家严重的心理健康状况。 为了更好地理解IA的临床意义,本研究在统计学上测试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说明了有助于疾病发展和维持的潜在认知机制。 该模型区分了广义网络成瘾(GIA)和特定形式。 本研究在一般互联网用户群体上测试了GIA模型。 来自1019用户的调查结果表明,假设的结构方程模型解释了GN症状方差的63.5%,通过网络成瘾测试的简短版本来衡量。 通过心理和人格测试,结果显示一个人的特定认知(不良应对和认知期望)增加了GIA的风险。 这两个因素介导了GIA的症状,如果存在其他风险因素,如抑郁,社交焦虑,自尊心低,自我效能低,以及高压力脆弱性,这些都是研究中测量的一些区域。 该模型表明,即使存在其他人格或心理脆弱性,具有较高应对技能且无法预期互联网可用于增加积极情绪或减少负面情绪的个人也不太可能参与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 对治疗的影响包括对GIA发展的明确认知成分以及评估患者应对方式和认知以及改善错误思维以减轻症状和参与康复的需要。
介绍
在许多研究中发现了对互联网的一个有问题的使用,并表明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导致失业,学业失败和离婚等持续的负面后果(评论见 格里菲斯,2000a,b; Chou等人,2005; Widyanto和Griffiths,2006; Byun等人,2009; Weinstein和Lejoyeux,2010; Lortie和Guitton,2013)。 这种现象的临床相关性在从1.5到8.2%的高估计患病率的背景下变得重要(Weinstein和Lejoyeux,2010)或甚至高达26.7%,具体取决于使用的比例和应用的标准(Kuss等人,2014).
虽然这个临床问题的第一次描述几乎是20年前(年轻,1996),分类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在科学文献中使用了几个术语,范围从“强制性互联网使用”(Meerkerk等,2006, 2009, 2010),“互联网相关问题”(Widyanto等,2008),“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Caplan,2002),“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戴维斯,2001)“与互联网相关的成瘾行为”(Brenner,1997),仅举几例。 然而,在过去的10年中,该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人员使用术语“网络成瘾”或“网络成瘾症”(例如, Johansson和Götestam,2004; Block,2008; Byun等人,2009; Dong等人,2010, 2011, 2013; Kim等人,2011; Purty等,2011; 年轻,2011b, 2013; Young等,2011; 周等人,2011; Cash等,2012; Hou等人,2012; Hong等人,2013a,b; Kardefelt-Winther,2014; Pontes等,2014; Tonioni等人,2014)。 我们也更喜欢“网络成瘾(IA)”一词,因为最近的文章(参见讨论) Brand等,2014)强调过度使用互联网与其他成瘾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 Grant等人,2013)以及物质依赖性(另见 年轻,2004; 格里菲斯,2005; Meerkerk等,2009)。 有人认为,与物质依赖的发展和维持相关的机制可以转移到互联网应用(以及其他行为成瘾)的成瘾性使用,例如成瘾的激励敏感理论和相关概念(例如, Robinson和Berridge,2000, 2001, 2008; Berridge等,2009)。 这也非常适合成瘾行为的组件模型(格里菲斯,2005).
已经对IA的心理相关性进行了许多研究,但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已经完成,而没有区分广义网络成瘾(GIA)和特定的网络成瘾(SIA; Moran-Martin和Schumacher,2000; 梁,2004; Ebeling-Witte等,2007; 卢,2008; 金和戴维斯,2009; Billieux和Van der Linden,2012),虽然心理机制可能不同,但也适用于不同的年龄组或使用的应用(Lopez-Fernandez等人,2014)。 我们的研究探讨了应对风格和认知期望对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在GIA的开发和维护中的作用,以便更好地理解潜在的机制以及对诊断和治疗的潜在影响。
在理论层面上,已经假定IA必须在广义互联网使用方面加以区分(格里菲斯和伍德,2000)与特定类型的IA相比,例如网络,网络关系,网络强迫(例如,赌博,购物),信息搜索和在线游戏,以发展对互联网的成瘾(例如, Young等,1999; Meerkerk等,2006; Block,2008; Brand等,2011)。 但是,DSM-5的附录中只包含一种子类型Internet Gaming Disorder(APA,2013)。 大多数研究或者将IA评估为统一构建体,或者仅评估一种特定亚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网络游戏)。 在他的认知 - 行为模型中, 戴维斯(2001) 也区分了广义病理性互联网使用(GIA)和特定病理性互联网使用(SIA)。 GIA被描述为互联网的多维度过度使用,常常伴随着时间浪费和非定向使用互联网。 特别使用互联网的社交方面(例如,通过社交网站的社交通信)(另见讨论) Lortie和Guitton,2013),这应该与缺乏社会支持以及个人在非虚拟情境中经历的社会缺陷有关。 此外,有人认为,受试者可能过度使用几种不同的互联网应用,而没有一个特定的喜欢,例如玩游戏,看色情,浏览信息和/或购物网站,发布自拍,在视频平台上观看视频,阅读博客其他人,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个人沉迷于互联网而不是沉迷于互联网(但也参见讨论 Starcevic,2013)。 戴维斯辩称,GIA和SIA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患有GIA的个人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类似的问题行为,而患有SIA的个人会在另一个环境中产生类似的问题行为。 在互联网,GIA和SIA的两种形式的上瘾使用中,建议对自我和世界的功能失调的认知发挥基础作用(Caplan,2002, 2005).
针对GIA的研究表明,因互联网使用而导致的日常生活中的主观抱怨与不同的人格特征相关。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GIA与精神病理学合并症有关,例如情感或焦虑症(Whang等,2003; Yang等人,2005; Weinstein和Lejoyeux,2010)以及人格特质羞怯,神经质,压力脆弱,拖延倾向和低自尊(Niemz等,2005; Ebeling-Witte等,2007; Hardie和Tee,2007; Thatcher等人,2008; 金和戴维斯,2009)。 此外,社会背景的因素,例如缺乏社会支持或社会隔离(Moran-Martin和Schumacher,2003; Caplan,2007)甚至在青少年的教育环境中的孤独感(Pontes等,2014),似乎与GIA有关。 此外,有人认为使用互联网作为应对有问题或有压力的生活事件的工具有助于GIA的发展(Whang等,2003; Tang等人,2014)。 IA患者也表现出冲动性应对策略的高度倾向(Tonioni等人,2014)。 一些作者甚至将IA概念化为应对日常生活或日常麻烦的一种(Kardefelt-Winther,2014)。 仍然只有一些初步研究明确比较了不同类型SIA的预测因子。 Pawlikowski等。 (2014) 据报道,羞怯和生活满意度与网络游戏的上瘾使用有关,但与病态使用网络游戏或使用游戏和网络游戏无关。
基于以前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论证的论点 戴维斯(2001)我们最近发表了关于GIA和SIA开发和维护的理论模型,并且还考虑了当前关于在互联网上成瘾的受试者的神经心理学和神经影像学发现的文献。Brand等,2014)。 在使用社交网站的背景下已经提到了模型中包含的一些方面,例如预期的积极结果(Turel和Serenko,2012)。 还有研究表明,在线拍卖的过度或令人上瘾的使用与个人对该技术的信念的变化相关,这决定了未来的使用和使用意图(Turel等,2011)。 这符合我们关于GIA的理论模型,其中我们假设关于互联网可以为一个人做什么的信念或期望会影响行为,即互联网的使用,这反过来也会影响未来的预期。 然而,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专注于预期和应对策略在开发和维护GIA以及特定类型的SIA中的中介作用。
对于GIA的开发和维护,我们认为用户具有某些需求和目标,可以通过使用某些Internet应用程序来实现。 基于先前的研究,我们将这些研究结果中的一些纳入其中,以开发一个将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的综 最初,一个人的核心特征与IA相关,包括精神病理学方面,人格方面和社会认知。 在第一部分,我们包括精神病理症状,特别是抑郁症和社交焦虑症(例如, Whang等,2003; Yang等人,2005),功能失调的人格方面,如低自我效能,羞怯,压力易损性和拖延倾向(Whang等,2003; Chak和Leung,2004; Caplan,2007; Ebeling-Witte等,2007; Hardie和Tee,2007; Thatcher等人,2008; 金和戴维斯,2009; Pontes等,2014),社会孤立/缺乏社会支持(Moran-Martin和Schumacher,2003; Caplan,2005)在GIA的发展。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人的主要特征和认知对互联网成瘾性使用的发展的影响应该通过某些与互联网相关的认知来调节,特别是互联网使用预期(Turel等,2011; Xu等人,2012; Lee等人,2014),以及应对日常生活要求或日常麻烦的某些策略(Tang等人,2014; Tonioni等人,2014)。 在模型的第三部分中,作为一种随之而来的行为,如果用户上网并且在功能失调的情况下应对问题或负面情绪并且人们期望互联网使用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负面情绪,那么可能他们会转向互联网,以逃避失去控制,糟糕的时间管理,渴望和增加社会问题所证明的那种感受。 在关于物质相关疾病的发展和维持的文献中已经很好地描述了强化和调理过程的作用(例如, Robinson和Berridge,2001, 2008; Kalivas和Volkow,2005; Everitt和Robbins,2006)。 我们还认为,应对方式和互联网使用预期的积极和消极强化相继导致失去对互联网使用的认知控制,这是由前额(执行)功能调节的(Brand等,2014).
虽然这个模型非常适合以前有关IA背后心理机制的重要发现的文献(见 Kuss和Griffiths,2011a,b; 格里菲斯,2012并且还与最近的GIA和不同类型的SIA的神经心理学和神经影像学相关(Kuss和Griffiths,2012; Brand等,2014),该模型仍需要增量有效性方面的经验证据。 在本研究中,我们的目的是将上述GIA理论模型中总结的假设转化为潜在变量水平的统计模型,并使用大规模的互联网人群测试预测因子和介质对GIA症状严重程度的影响。 使用经过验证的心理和人格测量,我们首先评估一个人的核心特征,以一种普遍的方式预测互联网的过度和令人上瘾的使用。 使用经过验证的应对措施和新开发的互联网使用预期衡量标准,我们测试了不良的应对技巧和互联网使用预期(例如使用互联网逃避负面情绪或不愉快的情况)调解人的核心特征与症状之间的联系。 GIA。
材料和方法
可操作模型
我们首先翻译了介绍中描述的理论模型,并在文章中进行了说明 Brand等。 (2014) 进入可测试和可操作的统计模型。 对于理论模型中提到的每个维度,我们选择至少两个显式变量来构建潜在级别的结构方程模型(SEM)。 对于每个变量,我们然后使用特定的比例(每个由几个项目组成,参见下面的工具的描述)来操作清单变量。 该潜在水平的SEM操作模型如图所示 1.
主题
通过全面的在线调查,我们有1148受访者。 由于心理测量量表中的数据不完整而排除129参与者后,最终样本包括 N = 1019。 参与者通过广告,互联网平台(一般心理学团队的Facebook帐户:认知),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学生的电子邮件列表,以及当地酒吧和酒吧的传单以及词汇来招募。嘴里的建议。 广告,电子邮件和传单包括一个声明,参与者可以参加有机会赢得以下项目之一:(1)iPad,(2)iPad mini,(3)iPod nano,(4) )iPod shu ffl e,20亚马逊礼品卡(每个50欧元)。 该研究得到了当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最终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5.61岁(SD = 7.37)。 样本包括625名(61.33%)女性和385名(37.78%)男性(九名志愿者未回答此问题)。 关于私人生活状况,有577名参与者(56.62%)生活在婚姻关系中或已婚,有410名参与者(40.24%)表示目前没有恋爱关系(32名参与者未回答此问题)。 在评估时,有687名参与者(67.42%)是学生,有332名参与者(32.58%)有固定工作(我们没有学历)。 在整个样本中,有116名参与者(11.4%)满足了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标准[在简短的Internet成瘾测试(s-IAT)中,临界值> 30,请参阅下面的工具说明],而有38名参与者(3.7%) Internet的病理使用(s-IAT中> 37)。 平均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为972.36分钟/周(SD = 920.37)。 在整个样本中,有975个人使用了社交网络/通讯站点(M分钟/周 = 444.47,SD = 659.05),998个人(97.94%)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M分钟/周 = 410.03,SD = 626.26),988个人(96.96%)使用购物网站(M分钟/周 = 67.77,SD = 194.29),557参与者使用在线游戏(54.66%, M分钟/周 = 159.61,SD = 373.65),在线赌博由161参与者完成(15.80%, M分钟/周 = 37.09,SD = 141.70),485个人使用cybersex(47.60%, M分钟/周 = 66.46,SD = 108.28)。 关于多个Internet应用程序的使用,995参与者(97.64%)报告定期使用上述三个或更多个Internet应用程序。
仪器功能
短网瘾测试(s-IAT)
使用德国短版网络成瘾测试评估IA的症状(Pawlikowski等,2013),这是基于由开发的原始版本 年轻(1998)。 在短版(s-IAT)中,必须以12分制回答1个项目,分数范围为5(从不)到12(非常频繁),导致总分从60到30不等,而得分> 37表示互联网使用有问题,得分> XNUMX表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awlikowski等,2013)。 s-IAT包括两个因素:失去控制/时间管理和渴望/社会问题(每个有六个项目)。 虽然12项目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加载了两个因素(CFA; Pawlikowski等,2013),它们捕获了IA的关键症状,例如在组件模型中描述的(格里菲斯,2005)。 第一个分量表“失去控制/时间管理”评估一个人因日常生活中因日常生活而遭受时间管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例如,“你经常忽视家务劳动花费更多时间在网上?”和“你有多少经常因深夜上网而失眠?”)。 此子量表的项目还评估因互联网使用过度而导致的负面后果(例如,“您的成绩或学校工作多长时间因您在线消费的时间而受到影响?”)。 还可以测量受试者是否失去对互联网使用的控制权以及他们是否曾试图减少他们的互联网使用并且失败(例如,“您多久发现一次网上停留的时间比您预期的要长?”和“多久一次?”你试图减少你在网上花费的时间和失败吗?“)。 所有项目都不衡量在线时间,但是个人是否因互联网使用而失去对互联网使用和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的控制。 第二个分量表“渴望/社会问题”衡量了过度使用互联网对社交互动的影响以及对媒体的关注(例如,“你常常在互联网上常常关注互联网,或幻想在线?”)。 这个子量表的项目还可以评估人际关系问题(例如,如果有人在你上网时困扰你,你会多久拍一下,大喊大叫或行动烦恼?)和情绪调节(例如,“你多久经常感到沮丧,喜怒无常你是谁,或者当你重新上线后就会消失? 所有项目通常包括术语“互联网”或“在线”,而不关注某个应用程序。 在指示中,参与者被告知所有问题都与他们对因特网的一般使用有关,包括所有使用的应用程序。
s-IAT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属性和有效性(Pawlikowski等,2013)。 在我们的样本中,内部一致性(Cronbach的α)是整个规模的0.856,0.819是控制/时间管理的因素损失,0.751是因素渴望/社会问题。
简要症状库存 - 分量表抑郁症
抑郁症的症状用德语版本评估(弗兰克,2000)简短症状量表的分量表压低(Boulet和Boss,1991; Derogatis,1993)。 该量表包括评估最近7天抑郁症状的六个项目。 答案必须以五分制给出,范围从0(=完全没有)到4(=极端)。 我们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是0.858。
简要症状库存 - 子量表人际关系敏感度
用德语版评估社交焦虑和人际关系敏感性的症状(弗兰克,2000)简短症状量表的子量表人际关系敏感度(Boulet和Boss,1991; Derogatis,1993)。 该量表由四个项目组成,答案必须以五分制给出,范围从0(=完全没有)到4(=极端)。 我们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是0.797。
自尊量表
通过自尊量表评估自尊(罗森伯格,1965)。 我们这里使用了修改后的德语版本(Collani和Herzberg,2003),由十个项目组成。 答案必须以四分制给出,范围从0(=非常不同意)到3(=非常同意)。 我们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是0.896。
自我效能量表
通过自我效能量表评估自我效能(施瓦泽和耶路撒冷,1995),由10项目组成。 答案必须以四分制给出,范围从1(=不是真)到4(=完全正确)。 我们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是0.863。
特里尔慢性压力量表
通过特里尔慢性压力量表的筛选版本测量应激脆弱性(TICS; Schulz等人,2004)。 筛选包含有关最近12个月的压力暴露的3项目。 每个陈述必须以从0(=从不)到4(非常经常)的五个等级来回答。 我们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是0.908。
寂寞规模
Loneliness Scale的简短版本(De Jong Gierveld和Van Tilburg,2006)用于衡量孤独感(子量表情感孤独,三项)和感知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子量表,三项)。 所有陈述都必须从1(= no!)到5(= yes!)以五分制回答。 在我们的样本中,内部一致性(Cronbach的α)是用于子量表情感孤独的0.765和用于子量表社会支持的0.867。
COPE简介
简要COPE(Carver,1997)测量几个不同子域中的应对方式。 我们这里使用了德语版的三个分量表(Knoll等,2005):否认,物质使用和行为脱离。 每个子量表由两个项目表示,必须以四点量表来回答,范围从1(我完全没有这样做)到4(=我已经做了很多)。 我们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是用于子量表拒绝的0.561,用于子量表物质使用的0.901,以及用于子量表行为脱离的0.517。 鉴于该量表仅包含两个项目,并且鉴于该仪器已用于多项验证研究,包括重新测试可靠性的报告,我们认为可靠性是可接受的。
互联网使用期望量表
为了评估互联网使用预期,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规模 - 在第一个版本中 - 包含16项目。 这些项目反映了一些核心激励因素,例如报告 徐等人。 (2012) 并通过 怡(2006)。 物品已分配 先验 两个尺度(每个有八个项目):互联网使用预期反映积极强化(例如,“我使用互联网体验快乐”)和反映负面强化的那些(例如,“我使用互联网分散注意力”)。 所有答案都是以六分制给出的,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6(=完全同意)。 根据我们在本研究中收集的数据(N = 1019),我们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号角(1965) 并行分析和最小平均部分(MAP)测试(Velicer,1976)用于确定适当数量的因素。 该程序产生了稳定的双因素解决方案。 然后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超常旋转的全民教育,以评估互联网使用期望量表(IUES)的结构。 全民教育的结果以IUES的最终8项目版本结束,双因素结构仍然存在(表格) 1)。 有了这两个因素,我们观察到了63.41%的方差解释。 第一个因子包含四个项目,其中主要因子的负荷较高(> 0.50),而另一个因子的负荷较低(<0.20),并且与正期望相关,因此我们将此因子称为“正期望”。 第二个因素包括四个因素,其中主要因素的负荷较高(> 0.50),其他因素的负荷较低(<0.20),并且所有与Internet相关的项目均用于避免或减少负面情绪或想法,因此我们将其命名为因素“避免期望”。 这两个因素都具有良好的可靠性(“正期望”:Cronbach的α= 0.832和“回避期望” Cronbach的α= 0.756)。 这两个因素显着相关(r = 0.496, p <0.001)具有中等效果(科恩,1988).
为了确保仪器的因子结构,我们评估了应用CFA的169受试者的另外样本(平均年龄= 21.66,SD = 2.69; 106女性)。 CFA是用MPlus完成的(Muthén和Muthén,2011)。 为了评估模型拟合,我们应用了标准标准(Hu和Bentler,1995, 1999):标准化的均方根残差(SRMR;低于0.08的值表示与数据的良好拟合),比较拟合指数(CFI / TLI;高于0.90的值表示良好拟合,高于0.95的值非常合适)和均方根近似误差(RMSEA;“紧密拟合测试”;低于0.08且显着性值低于0.05的值表示可接受的拟合)。 CFA证实了IUES的双因素解决方案具有良好至优秀的拟合参数:RMSEA为0.047,CFI为0.984,TLI为0.975,SRMR为0.031。 χ2 测试不显着,χ2 = 24.58, p = 0.137表示数据没有显着偏离理论模型(两个因素解决方案,如表中所示) 1)。这个样本仅用于CFA。 数据未包括在进一步分析中。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1.0 for Windows(IBM SPSS Statistics,发布的2012)执行统计标准程序。 计算Pearson相关性以测试两个变量之间的零阶关系。 为了控制异常值的数据,我们创建了一个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其平均标准差与我们在s-IAT(总分)中发现的相同。 如果相关性不受数据中异常值的影响,则该随机变量在理论上应与所有感兴趣的变量无关。 与随机变量的所有相关性都非常低, rs <0.049,表明最终样本中的任何量表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异常值(N = 1019)。 另外,视觉上控制变量之间的散点图。 同样,没有找到极端异常值。 因此,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分析。
使用MPlus 6计算SEM分析(Muthén和Muthén,2011)。 没有丢失的数据。 在测试完整模型之前,还使用MPlus中的CFA测试了潜在尺寸的拟合。 对于SEM和CFA两者,应用最大似然参数估计。 为了评估模型拟合,我们应用了标准标准(Hu和Bentler,1995, 1999)如之前的部分所述。 根据,要求应用调解员分析 男爵和肯尼(1986),调解中包含的所有变量应相互关联。 我们还使用适度回归来分析潜在的主持人效应,作为对应对概念的替代概念化的额外分析。
成果
描述性值和相关性
样本在s-IAT中的平均分数和所有其他应用的分数可以在表中找到 2。 平均s-IAT得分 M = 23.79(SD = 6.69)与报告的得分相当 Pawlikowski等。 (2013) 对于一般人群的1820受试者样本(平均s-IAT得分为 M = 23.30,SD = 7.25)。 s-IAT(总分)与问卷和分数表中的分数之间的双变量相关性如表所示 3.
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拟议模型的潜在维度
为了系统地测试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我们首先分析了因子模型,这意味着测试潜在维度是否可以由显性变量可接受地表示。 因此,CFA使用六个潜在维度(一个依赖维度,三个预测维度,两个介体维度)执行。 RMSEA是0.066 p <0.001,CFI为0.951,TLI为0.928,SRMR为0.041,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第一个潜在维度“GIA的症状”很好地表现为s-IAT(失去控制/时间管理和渴望/社交问题)两个因素的得分。 第一个预测变量“精神病理症状”由BSI的两个分量表(抑郁和人际关系敏感性)显着代表。 “人格方面”维度很好地表现为三个假设的显性变量(自我效能,自尊和压力脆弱性),最后一个预测维度“社会认知”由孤独量表的两个分量表(情绪化)表示得很好。孤独和社会支持)。 结果表明,第一个假设的中介维度“应对”很好地代表了COPE的三个分量表(否定,滥用药物和行为脱离),第二个中介维度“互联网使用预期”很好地代表了两个IUES因素(积极的预期和避免预期)。
总体而言,CFA表明潜在维度由明显变量可接受地表示。 只有在应对规模物质滥用的维度中,因子载荷较弱(β= 0.424)但仍然显着(p <0.001),因此,考虑到整个模型与数据吻合得很好,因此就足够了。 表中显示了所有因子载荷和标准误差 4.
完全结构方程模型
所提出的以GIA为因变量的潜在维度的理论模型(由两个s-IAT因子建模)产生了与数据的良好拟合。 RMSEA是0.066 p <0.001,CFI为0.95,TLI为0.93,SRMR为0.041。 χ2 测试显着,χ2 = 343.89, p <0.001,鉴于大样本量,这是正常的。 但是,χ2 对于基线模型的测试也是显着的,具有广泛更高的χ2 值,χ2 = 5745.35, p <0.001。 总之,数据与所提出的理论模型非常吻合。 总体而言,完整的SEM可以很好地解释GIA中63.5%的大部分差异(R2 = 0.635, p <0.001)。 该模型以及所有直接和间接影响如图XNUMX所示。 2.
预测因子对GIA的所有三种直接影响都不显着(图 2)。 但请注意,潜在变量精神病理学方面的直接影响略微未能达到显着性 p = 0.059。 在这里,必须考虑到β-体重是负的,这表明 - 如果有人会解释边缘显着的直接影响 - 如果来自精神病理学方面的间接影响,高抑郁症和社交焦虑与GIA的症状较低同时发生两个中介变量(应对和互联网使用预期)被分开。 两个潜在预测变量的精神病理学方面和个性对潜在中介变量应对和互联网使用预期的直接影响是显着的。 相比之下,潜在变量社会认知对应对和互联网使用预期的直接影响并不显着,这意味着当控制其他两个潜在维度的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显着。
然而,社会认知对互联网使用预期的影响略微未达到意义 p = 0.073。 应对GIA的直接影响(p <0.001)和互联网使用预期(p <0.001)具有显着的效应大小。
从精神病理学方面对应对GIA的间接影响是显着的(β= 0.173,SE = 0.059, p = 0.003)。 此外,从互联网使用预期到GIA的精神病理学方面的间接影响是显着的(β= 0.159,SE = 0.072, p = 0.027)。 从人格方面到应对GIA的间接影响也很显着(β= -0.08,SE = 0.041, p = 0.05),但效果大小非常小。 人格方面对互联网使用预期的间接影响是显着的(β= -0.160,SE = 0.061, p = 0.009)。 社会认知对应对的间接影响(β= 0.025,SE = 0.030, p = 0.403)和互联网使用预期的社会认知(β= -0.08,SE = 0.045, p = 0.075)到GIA并不重要。 具有所有因子载荷的模型 β- 重量如图所示 2。 潜在维度的精神病理学方面与潜在的维度人格方面显着相关(r = 0.844, p <0.001)和潜在维度的社会认知(r = -0.783, p <0.001)。 此外,两个潜在维度的人格方面和社会认知也相互关联(r = 0.707, p <0.001)。
其他分析
所描述的模型是理论上争论的模型,因此我们首先测试的模型。 然而,我们之后分别测试了一些其他模型或模型的部分,以便更详细地更好地理解GIA的基础机制。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精神病理学对GIA的影响,因为我们发现有趣的是SEM中的直接影响(尽管不显着)是负面的(见图) 2),虽然在双变量水平上,相关性是积极的。 具有精神病理学方面(以BIS抑郁和BSI社交焦虑为代表)作为预测因子和GIA(由两个s-IAT因子表示)作为因变量的简单模型具有良好的模型拟合(所有拟合指数均优于可接受的)和效果是积极的(β= 0.451, p <0.001)。 我们还计算了没有两个介体的模型,这意味着心理病理方面,人格方面和社会方面可以作为直接预测因素,而GIA是因变量(所有潜在变量都与整个SEM中使用的变量相同,见图XNUMX)。 2)。 没有介体的模型也具有良好的拟合指数(有一个例外:RMSEA与0.089有点高),对GIA(两个s-IAT因子)的直接影响是:精神病理学方面对GIAβ= 0.167的影响, p = 0.122; 人格方面对GIAβ= -0.223的影响, p = 0.017; 和社会方面对GIAβ= -0.124的影响, p = 0.081。 请注意,当对人格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进行控制时,精神病理学方面对GIA的影响在该模型中仍然是积极的(但不显着)。 总的来说,整体扫描电镜的结果可以说明两种调解员(应对和预期)对精神病理学方面对GIA影响的完全调解,另外两项分析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表明对双变量水平的正面影响并且通过包含其他变量作为预测变量来简化简单模型。
我们理论上将应对概念化为调解者(Brand等,2014)。 然而,人们也可能会争辩说,应对不会调解精神病理学方面的影响,而是扮演主持人的角色。 为了确保应对作为调解者而不是主持人的概念化是合适的,我们还使用适度回归分析计算了一些主持人分析。 例如,当使用精神病理学方面作为预测因子,应对作为主持人,以及s-IAT(总和得分)作为因变量时,精神病理学方面(β= 0.267)和应对(β= 0.262)解释了s-IAT的方差。显着(两者都有 p <0.001),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能显着增加方差解释( R2 = 0.003, p = 0.067,β= -0.059)并且慢化剂效应的增量几乎为零(0.3%)。
我们还将年龄和性别视为可能对模型结构产生影响的潜在变量。 为了测试这一点,我们首先计算了年龄与所有其他变量之间的双变量相关性,导致相关性非常低。 只有一个相关性 r = 0.21(年龄和避免预期),这仍然是一个低效果(科恩,1988),以及所有其他相关性之间的影响 r = 0.016和 r =大多数是0.18 r <0.15并且 r <0.10。 年龄与s-IAT之间的相关性也很低 r = -0.14(虽然很重要 p <0.01,在如此大的样本中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未将年龄纳入调解模型的要求(男爵和肯尼,1986)我们决定不将年龄纳入另一个模型。 在性别方面,我们比较了所有所用量表的群体平均得分,发现只有一个有意义的群体差异(BSI社交焦虑,女性得分较高,效果较差) d = 0.28,所有其他效果均低于0.28,对s-IAT得分的影响为 d = 0.19)。 然而,我们使用SEM分析中的平均结构分析测试了女性和男性的模型结构是否不同。 这意味着我们测试了SEM(见图 2)对于男性和女性参与者来说是平等的。 该测试的H0是:理论模型=“男性”组的模型=“女性”组的模型。拟合指数都是可接受的,表明男女关系的结构没有显着差异。 RMSEA是0.074 p <0.001,CFI为0.93,TLI为0.91,SRMR为0.054。 χ2 测试显着,χ2 = 534.43, p <0.001,鉴于大样本量,这是正常的。 但是,χ2 对于基线模型的测试也是显着的,具有广泛更高的χ2 值,χ2 = 5833.68, p <0.001。 对χ的贡献2 男性和女性测试模型的可比性(χ2 女性的贡献= 279.88,χ2 男性贡献= 254.55)。 虽然模型的整体结构对于男性和女性没有显着差异,但我们检查了简单的路径并发现了三个不同之处。 从人格方面到应对的路径在男性中很重要(β= -0.437, p = 0.002),但不是女性(β= -0.254, p = 0.161)和人格方面对预期的影响在男性中是显着的(β= -0.401, p = 0.001),但不是女性(β= -0.185, p = 0.181)。 此外,精神病理学方面对女性的预期效果显着(β= 0.281, p = 0.05),但不是男性(β= 0.082, p = 0.599)。 所有其他效果和潜在维度的表示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差异,也与图中所示的整体模型没有差别 2。 总之,所测试的整个模型对男性和女性都有效,尽管人格方面对应对和预期的负面影响在男性中比女性更为明显,而女性则存在精神病理学方面对预期的影响,但男性则不然。 。
讨论
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用于开发和维护互联网上瘾的使用(Brand等,2014),这是基于主要论点 戴维斯(2001) 他们首先建议区分广义的过度使用互联网(GIA)和某些互联网应用(SIA)的特定成瘾。 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们将GIA上的理论模型转换为潜在水平的操作模型,并使用对1019受访者的互联网人群的在线调查对SEM进行统计测试。 我们发现整体良好的模型符合数据和假设的SEM,它代表理论模型的主要方面,并解释了由s-IAT测量的GIA症状的63.5%变化(Pawlikowski等,2013).
该模型是第一个将与IA相关的元素联系在一起的模型,如抑郁,社交焦虑,低自尊,低自我效能和较高的压力脆弱性。 基于与发展IA相关的认知的重点和一般的成瘾行为(刘易斯和奥尼尔,2000; Dunne等,2013; Newton等,2014),该模型调查两个中介变量(应对方式和互联网使用预期)是否影响预测变量(精神病理学,人格和社会认知)对GIA发展的直接影响。 结果表明,应对方式和互联网使用预期都起着重要作用。
包含在模型中的所有变量(预测因子和介质)与双变量水平上的s-IAT得分显着相关。 这与先前关于IA症状与人格方面,精神病理症状和其他人变量之间的双变量关系的研究基本一致,如引言中所述。 然而,在SEM分析中,当将假设的介体包括在模型中时,三个主要预测因子(在潜在维度上)的所有直接影响都不再显着。 这意味着精神病理学方面(抑郁,社交焦虑),人格方面(自尊,自我效能和压力脆弱性)以及社会认知(情感孤独,感知社会支持)不会直接影响GIA的症状,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是由功能失调的应对方式或互联网使用预期,或两者兼而有之。 然而,精神病理学方面和人格方面显着预测了功能失调的应对方式和互联网使用预期。 然而,当社会认知的相对影响受精神病理学和人格方面的影响控制时,社会认知与应对和预期并不显着相关(但请注意,三个预测因素潜在维度相关,社会认知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预期略微未达到意义)。 应对方式和预期对GIA症状的直接影响是显着的。 总之,目前的研究虽然有非临床人群,但不仅证实了先前关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和处理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发现(Kardefelt-Winther,2014; Tang等人,2014; Tonioni等人,2014)以及互联网使用预期(Turel和Serenko,2012; Xu等人,2012; Lee等人,2014)用于发展或维持GIA的症状,但明确强调应对和预期作为GIA基础过程中的调解者的作用。
该模型使用大量在线人群进行测试。 模型必须使用明确定义的临床样本进行测试,例如寻求治疗的个体。 该模型的含义将更加强大,临床人群可以得出更准确的临床意义。 尽管11.3%的样本报告了互联网使用存在问题且3.7%将自己描述为具有令人上瘾的互联网使用,但本研究仅被视为初步观察模型是否有效并得出可能具有临床相关性的统计推断。 然而,作为一个具有统计意义的新模型,使用对在线用户的各种心理和性格测试,可以谨慎地做出一些可能激发未来研究的临床意义。
首先,具有功能失调的应对以解决其生活中的问题以及期望互联网可用于增加积极或减少消极情绪的个体可能更有可能发展GIA。 此外,精神病理学方面对功能失调的应对和互联网使用预期的影响是积极的,表明抑郁症和社交焦虑症的高症状可能增加功能失调的应对策略的风险,也可能增加互联网为应对压力或负面提供帮助的预期。心情。 只有当这些过程协同行动,意味着精神病理症状和应对/预期的结合时,使用互联网上瘾的可能性似乎才会增加。
其次,尽管针对GIA治疗的研究数量有限,但荟萃分析发表于 温克勒等人。 (2013) 认为认知行为疗法是首选方法。 这尤其基于对在线时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治疗效果的分析。 事实上,IA的认知行为疗法(CBT-IA; 年轻,2011a)已被确定为治疗IA的最普遍形式(Cash等,2012)。 在GIA的认知行为治疗中提出 年轻(2011a)个人特征以及应对和互联网使用期望已被假设为与GIA的治疗相关,但经验证据非常稀少(例如, 年轻,2013).
本研究中提供的研究结果提供了另一个证据来源,表明认知行为疗法和CBT-IA可用于治疗IA。 该人的特定认知(应对方式和互联网使用预期)调节精神病理症状(抑郁,社交焦虑),人格特质和社会认知(孤独,社会支持)对GIA症状的影响。 使用认知疗法,评估的重点应该包括识别需要解决的功能失调的认知。 也就是说,经过检查,临床医生应检查互联网使用预期,以了解客户的需求以及客户认为互联网可能有助于满足的方式。
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治疗应该解决与互联网功能失调相关的适应不良认知问题。 这些研究结果证实早期的研究表明,适应不良的认知,如过度概括,避免,抑制,放大,适应不良问题解决,或消极的自我概念与上瘾的互联网使用相关(年轻,2007)。 这些研究结果的临床意义在于,治疗应该应用认知重组和重构,以打击导致上瘾使用互联网的想法。 例如,患有GIA的患者可能有社交焦虑和害羞的迹象,因此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也会在学校遇到其他人的麻烦。 然后,她可能会认为通过社交网站与其他人交流可以满足她的社交需求,而不会有“真正的”社交互动的可怕情境方面。 此外,她也可能期望玩在线游戏可能会分散她在学校的问题,并且在线购买或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可能会减少孤独感。 治疗将集中于在学校或私人生活中寻找其他地方,在那里她可以建立自尊和满足社会需求。 如果她不再证明社交网站,游戏和购物网站是她对自己生活感觉良好的唯一地方,并且她找到了其他更健康的网点,那么她对不同的互联网应用程序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 了解认知在GIA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认知疗法可以帮助客户重新构建使他们保持在线的假设和解释。 同样,研究结果的这些潜在临床意义必须谨慎对待,因为它们必须在寻求治疗的临床样本中复制。
然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些发现可以深入了解治疗师如何将CBT-IA专门应用于网络成瘾患者。 行为修改可以帮助客户开发和调整新的和更具功能性的应对策略,以应对日常的麻烦。 治疗需要专注于帮助客户找到更健康的应对方式,而不是转向互联网。 CBT-IA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行为疗法,以帮助客户应对导致IA,特定或一般化的潜在问题(年轻,2011a, 2013)。 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应对技能将减少客户上网的需求。 虽然在一般人群的样本中进行了研究,但我们认为应对和期望是GIA发展和维持的调解者的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GIA的机制,并且它们可能具有一些治疗意义,如上所述。 在当前研究中没有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前额皮质完整性的作用。 CBT-IA的功效还可以取决于患者的前额功能,因为在治疗过程中加强对因特网使用的认知控制很可能与执行功能和其他高阶认知过程有关。 这对于未来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IA患者的前额皮质功能可能会降低(参见概述) Brand等,2014).
在我们的样本中,年龄与GIA的症状呈负相关,但影响大小非常小(仅解释1.96%的方差)。 考虑最近有关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文章(例如, 伊士曼和Iyer,2004; Vuori和Holmlund-Rytkönen,2005; 坎贝尔,2008; 尼姆罗德,2011),除了年龄对使用互联网的几个方面的影响,例如使用动机和老年人在互联网上体验乐趣和满足感的方式,当然可以。 鉴于老年人由于前额皮质随年龄增长而变化,也有更高的机会发生执行功能障碍(Alvarez和Emory,2006),这也与减少决策有关(品牌和Markowitsch,2010),有人可能会推测,那些在互联网上经历了大量愉悦的行政人员减少的老年人可能会发展GIA。 但是,我们的数据并未表示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样本不包括较旧的主题。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调查与老年人GIA风险相关的特定脆弱性因素。
性别不影响模型的整体结构。 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发现针对特定类型的IA的性别影响,例如在线游戏(例如, Ko等人,2005)特别是cybersex(Meerkerk等,2006; 格里菲斯,2012; Laier等,2013, 2014),但也有人认为,两性都有发展上瘾互联网的风险(Young等,1999, 2011)。 在我们的研究中,通过s-IAT测量的性别对GIA的影响非常低(d = 0.19,见结果),表明至少在一般人群中,性别同样有发展GIA的风险。 虽然性别不影响扫描电镜的一般数据结构,但是从预测变量到调解员的三个直接影响,男女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如结果部分所述,精神病理学方面对女性而非男性的预期产生影响,人格方面对应对和预期的负面影响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更为明显。 这些影响符合有关抑郁和社交焦虑的性别差异的文献(Sprock和Yoder,1997; Moscovitch等,2005),以及自尊和自我效能(黄,2012)。 然而,作为研究重点的方面,即应对和预期的中介效应及其对GIA的重要性不受性别影响(参见平均结构分析的结果)。 因此,无论性别如何影响社交焦虑,抑郁或某些人格方面,应该在两性中的CBT-IA中考虑应对和预期。
最后,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 这是一个新开发的模型,需要对临床人群进行进一步测试,以充分发现其在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它也应该使用较长版本的IAT进行测试(年轻,1998; Widyanto和McMurran,2004)作为文献中更加测试的措施。 我们使用较短的版本给出了我们用于整个模型的评估工具的长度,但如果用临床样本复制这项工作,则建议使用IAT以及IA的其他测量,例如互联网评估和计算机游戏成瘾作为量表(AICA-S)或临床访谈(AICA-C)由临床组开发和验证(Wölfling等,2010, 2012)。 此外,为了本研究的目的,我们开发并测试了互联网使用预期问卷。 虽然我们在方法上保守且谨慎地制定了量表,但应该对其他人群的有效性进行评估,问卷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其他更详细的量表和访谈也应适用于临床样本,因为我们研究中评估的大多数方面都是使用简短的问卷来衡量的,由于实际原因(在线调查的时间限制) 。 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常见的方法差异(Podsakoff等人,2003)。 不幸的是,没有明确的标记变量,理论上与所有其他变量无关,由于实际原因已被纳入研究中(该调查花费了大约25 min,这是在线调查的关键阈值)。 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常见方法方差对结果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不太可能导致报告的整个数据结构。 检查双变量相关性时(表 3)可以看到其中一些非常低(例如, r = -0.08, r = -0.09, r = 0.12等)。 我们认为这些低相关性为假设共同方法方差不会显着影响主要分析提供了一些温和的提示。 尽管如此,该模型应该采用系统的多特征 - 多方法方法进行测试(Campbell和Fiske,1959)在未来的研究中。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GIA上,这意味着SIA上的模型如下所述 Brand等。 (2014),仍然需要根据经验进行测试。 应测试不同形式的SIA(例如,游戏,在线色情或互联网赌博),以确定应对技能和互联网使用预期在问题的发展中是否起到类似的作用。 如果GIA的概念主要足以涵盖患者的问题行为,那么这仍然是一个争论。 我们发现了与非特定使用几种不同互联网应用程序相关的自我报告问题与模型中建议的变量之间的联系的证据。 GIA的概念由s-IAT指令和项目公式实施,但也有超过97%的参与者报告经常使用三种或更多不同的互联网应用程序,如通信,游戏,赌博,网络,购物或寻求信息。 从临床角度来看,如果GIA可以成为寻求治疗的理由,或者寻求治疗的患者基本上只能使用某种应用失去对某一应用的控制,那么这仍是一个争论话题。 我们建议在临床研究中考虑这一点,系统地研究互联网使用环境中的关键行为,并分析多个互联网应用程序在临床样本中不受控制和上瘾使用的频率。 此外,并非GIA理论模型中提出的所有组件都可以包含在本研究中。 例如,未来的研究中可能包括其他人格特质或其他精神病理障碍。
结论
GIA模型的主要假设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 人的核心特征与GIA的症状有关,但这些影响是由人的特定认知调节的,特别是应对方式和互联网使用预期。 这些认知应该在治疗上瘾的互联网使用中得到解决。
作者贡献
马蒂亚斯·布兰德撰写了该论文的第一稿,监督了数据收集,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Christian Laier特别为实证研究和数据收集的概念化做出了贡献,并对手稿进行了修订。 Kimberly S. Young编辑了草案,对其进行了批判性修改,并在手稿上做出了智慧和实际的贡献。 所有作者最终都批准了这份手稿。 所有作者都对工作的所有方面负责。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研究是在没有任何可被解释为潜在利益冲突的商业或金融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
致谢
我们感谢Elisa Wegmann和Jan Snagowski对本研究和手稿的宝贵贡献。 他们帮助我们对在线调查和检查数据进行编程。
参考资料
Alvarez,JA和Emory,E。(2006)。 执行功能和额叶:荟萃分析评论。 Neuropsychol。 启示录 16, 17–42. doi: 10.1007/s11065-006-9002-x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APA。 (2013)。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5th Edn,华盛顿特区:APA。
Baron,RM和Kenny,DA(1986)。 社交心理研究中的主持人 - 中介变量区分:概念,战略和统计考虑。 J. Pers。 SOC。 心理学。 51,1173-1182。 doi:10.1037 / 0022-3514.51.6.1173
Berridge,KC,Robinson,TE和Aldridge,JW(2009)。 解剖奖励的组成部分:“喜欢”,“缺乏”和学习。 CURR。 奥平。 药理学。 9,65-73。 doi:10.1016 / j.coph.2008.12.014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Billieux,J。和Van der Linden,M。(2012)。 有问题地使用互联网和自我监管:对初步研究的回顾。 打开瘾君子。 J. 5,24-29。 doi:10.2174 / 1874941991205010024
Block,JJ(2008)。 DSM-V的问题:网络成瘾。 上午。 J.精神病学 165,306-307。 doi:10.1176 / appi.ajp.2007.07101556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Boulet,J。和Boss,MW(1991)。 简短症状清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心理学。 评估。 3,433-437。 doi:10.1037 / 1040-3590.3.3.433
Brand,M.,Laier,C.,Pawlikowski,M.,Schächtle,U。,Schöler,T。和Altstötter-Gleich,C。(2011)。 在互联网上观看色情图片:性唤起评级和心理 - 精神症状在过度使用互联网性爱网站时的作用。 Cyberpsychol。 Behav。 SOC。 网络。 14,371-377。 doi:10.1089 / cyber.2010.0222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Brand,M。和Markowitsch,HJ(2010)。 老龄化和决策:神经认知的观点。 老年学 56,319-324。 doi:10.1159 / 000248829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Brand,M.,Young,KS和Laier,C。(2014)。 前额控制和网络成瘾:理论模型和神经心理学和神经影像学发现的回顾。 面前。 哼。 神经科学。 8:375。 doi:10.3389 / fnhum.2014.00375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Brenner,V。(1997)。 计算机使用心理学:XLVII。 互联网使用,滥用和成瘾的参数: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的第一个90天。 心理学。 众议员。 80,879-882。 doi:10.2466 / pr0.1997.80.3.879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Byun,S.,Ruffini,C.,Mills,JE,Douglas,AC,Niang,M.,Stepchenkova,S.,et al。 (2009)。 网络成瘾:1996-2006定量研究的综合。 Cyberpsychol。 Behav。 12,203-207。 doi:10.1089 / cpb.2008.0102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Campbell,DT和Fiske,DW(1959)。 通过multitrait-multimethod矩阵进行收敛和判别式验证。 心理学。 公牛。 56,81-105。 doi:10.1037 / h0046016
坎贝尔,RJ(2008)。 满足老年人的信息需求:使用计算机技术。 家庭保健管理。 PRACT。 20,328-335。 doi:10.1177 / 1084822307310765
Caplan,SE(2002)。 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心理健康:基于理论的认知 - 行为测量工具的发展。 COMPUT。 哼。 Behav。 18, 553–575. doi: 10.1016/S0747-5632(02)00004-3
Caplan,SE(2005)。 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的社交技能帐户。 J. Commun。 55, 721–736. doi: 10.1111/j.1460-2466.2005.tb03019.x
Caplan,SE(2007)。 孤独感,社交焦虑和互联网使用问题之间的关系。 Cyberpsychol。 Behav。 10,234-242。 doi:10.1089 / cpb.2006.996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Carver,CS(1997)。 你想衡量应对,但你的协议太长了:考虑简短的COPE。 诠释。 J. Behav。 医学。 4, 92–100. doi: 10.1207/s15327558ijbm0401_6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Cash,H.,Rae,CD,Steel,AH和Winkler,A。(2012)。 网瘾:研究和实践的简要总结。 CURR。 精神病学 8,292-298。 doi:10.2174 / 15734001280352051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Chak,K。和Leung,L。(2004)。 羞怯和控制场所是网络成瘾和互联网使用的预测因素。 Cyberpsychol。 Behav。 7,559-570。 doi:10.1089 / cpb.2004.7.559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Chou,C.,Condron,L。和Belland,JC(2005)。 网络成瘾研究综述。 EDUC。 心理学。 启示录 17, 363–387. doi: 10.1007/s10648-005-8138-1
科恩,J。(1988)。 行为科学的统计功效分析 2nd Edn,Hillsdale,NJ:Erlbaum。
Collani,G。和Herzberg,PY(2003)。 Eine revidierte Fassung der deutschsprchigen SkalazumSelbstwertgefühlvonRosenberg。 Zeitrschr。 DIFF。 DIAGN。 斗志。 24,3-7。 doi:10.1024 // 0170-1789.24.1.3
戴维斯,RA(2001)。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 - 行为模型。 COMPUT。 哼。 Behav。 17, 187–195. doi: 10.1016/S0747-5632(00)00041-8
De Jong Gierveld,J。和Van Tilburg,TG(2006)。 针对整体,情感和社交孤独感的6项目量表:对调查数据进行确认测试。 RES。 老化 28,582-598。 doi:10.1177 / 0164027506289723
Derogatis,LR(1993)。 简要症状清单(BSI)。 管理,评分和程序手册,3rd Edn。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国家计算机服务。
Dong,G.,Lu,Q。,Zhou,H。和Zhao,X。(2010)。 网络成瘾患者的冲动抑制:来自Go / NoGo研究的电生理学证据。 神经科学 LETT。 485,138-142。 doi:10.1016 / j.neulet.2010.09.002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Dong,G.,Lu,Q。,Zhou,H。和Zhao,X。(2011)。 前体或后遗症:患有网络成瘾症的人的病理性障碍。 PLoS ONE的 6:e14703。 doi:10.1371 / journal.pone.001470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Dong,G.,Shen,Y.,Huang,J。和Du,X。(2013)。 网络成瘾患者的错误监测功能受损:与事件相关的FMRI研究。 欧元。 冰火。 RES。 19,269-275。 doi:10.1159 / 00034678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Dunne,EM,Freedlander,J.,Coleman,K。和Katz,EC(2013)。 冲动性,预期和预期结果的评估作为酒精使用和相关问题的预测因子。 上午。 J.药物滥用酒精 39,204-210。 doi:10.3109 / 00952990.2013.765005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Eastman,JK和Iyer,R。(2004)。 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和态度。 J. Consum。 营销 21,208-220。 doi:10.1108 / 07363760410534759
Ebeling-Witte,S.,Frank,ML和Lester,D。(2007)。 害羞,互联网使用和个性。 Cyberpsychol。 Behav。 10,713-716。 doi:10.1089 / cpb.2007.9964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Everitt,BJ和Robbins,TW(2006)。 药物成瘾的强化神经系统:从行为到习惯再到强迫。 纳特。 神经科学。 8,1481-1489。 doi:10.1038 / nn1579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Franke,GH(2000)。 简短症状invertory von LR Derogatis(Kurzform der SCL-90-R) - Deutsche Version。 哥廷根:Beltz Test GmbH。
Grant,JE,Schreiber,LR和Odlaug,BL(2013)。 现象学和行为成瘾的治疗。 能够。 J.精神病学 58,252-259。
Griffiths,MD(2000a)。 是否存在互联网和计算机“成瘾”? 一些案例研究证据。 Cyberpsychol。 Behav。 3,211-218。 doi:10.1089 / 109493100316067
Griffiths,MD(2000b)。 网络成瘾时间要认真对待? 冰火。 RES。 8,413-418。 doi:10.3109 / 16066350009005587
Griffiths,MD(2005)。 生物心理社会框架内成瘾的“组成部分”模型。 J. Subst。 使用 10,191-197。 doi:10.1080 / 14659890500114359
Griffiths,MD(2012)。 网络性成瘾:对实证研究的回顾。 冰火。 RES。 理论 20,111-124。 doi:10.3109 / 16066359.2011.588351
Griffiths,MD和Wood,RTA(2000)。 青春期的风险因素:赌博,视频游戏和互联网。 J. Gambl。 梭哈。 16,199-225。 doi:10.1023 / A:1009433014881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Hardie,E。和Tee,MY(2007)。 过度使用互联网:个人,孤独和社交支持网络在网络成瘾中的作用。 Austr。 J. Emerg。 TECHNOL。 SOC。 5,34-47。
Hong,S.-B.,Kim,J.-W.,Choi,E.-J.,Kim,H.-H.,Suh,J.-E.,Kim,C.-D。,et al 。 (2013a)。 网络成瘾男性青少年眶额皮质厚度减少。 Behav。 脑功能。 9, 11. doi: 10.1186/1744-9081-9-11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Hong,S.-B.,Zalesky,A.,Cocchi,L.,Fornito,A.,Choi,E.-J.,Kim,H.-H。,et al。 (2013b)。 网络成瘾青少年功能性大脑连接能力下降。 PLoS ONE的 8:e57831。 doi:10.1371 / journal.pone.0057831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Horn,JL(1965)。 因子分析中因素数量的基本原理和测试。 Psychometrika 30,179-185。 doi:10.1007 / BF02289447
Hou,H.,Jia,S.,Hu,S.,Fan,R.,Sun,W.,Sun,T.,et al。 (2012)。 网络成瘾患者的纹状体多巴胺转运蛋白减少。 J. Biomed。 生物技术。 2012,854524。 doi:10.1155 / 2012 / 854524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Hu,L。和Bentler,PM(1995)。 “评估模型适合度”,in 结构方程模型概念问题和应用,编辑。 RH霍伊尔。 (伦敦:Sage Publications,Inc。),76-99。
Hu,L。和Bentler,PM(1999)。 协方差结构分析中拟合指数的截止标准:常规标准与新备选方案。 结构。 恶趣。 造型 6,1-55。 doi:10.1080 / 10705519909540118
Huang,C。(2012)。 学业自我效能的性别差异:荟萃分析。 欧元。 J. Psychol。 EDUC。 28, 1–35. doi: 10.1007/s10212-011-0097-y
Johansson,A。和Götestam,KG(2004)。 网络成瘾:问卷的特征和挪威青年的流行(12-18年)。 SCAND。 J. Psychol。 45,223-229。 doi:10.1111 / j.1467-9450.2004.00398.x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Kalivas,PW和Volkow,ND(2005)。 成瘾的神经基础:动机和选择的病理学。 上午。 J.精神病学 162,1403-1413。 doi:10.1176 / appi.ajp.162.8.140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Kardefelt-Winther,D。(2014)。 对网络成瘾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论批评:针对互补性互联网使用的模型。 COMPUT。 哼。 Behav。 31,351-354。 doi:10.1016 / j.chb.2013.10.059
Kim,HK和Davis,KE(2009)。 走向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的综合理论:评估自尊,焦虑,流动和互联网活动的自我评估重要性的作用。 COMPUT。 哼。 Behav。 25,490-500。 doi:10.1016 / j.chb.2008.11.001
Kim,SH,Baik,S.-H.,Park,CS,Kim,SJ,Choi,SW和Kim,SE(2011)。 网络成瘾者减少纹状体多巴胺D2受体。 Neuroreport 22, 407–411. doi: 10.1097/WNR.0b013e328346e16e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Knoll,N.,Rieckmann,N。和Schwarzer,R。(2005)。 作为人格和压力结果之间的中介应对:白内障手术患者的纵向研究。 欧元。 J. Pers。 19,229-247。 doi:10.1002 / per.546
Ko,CH,Yen,J.-Y.,Chen,C.-C.,Chen,S.-H。和Yen,C.-F。 (2005)。 影响台湾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性别差异及相关因素。 J. Nerv。 换货。 派息。 193,273-277。 doi:10.1097 / 01.nmd.0000158373.85150.57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Kuss,DJ和Griffiths,MD(2011a)。 网络游戏成瘾:对实证研究的系统评价。 诠释。 J. Ment。 健康瘾君子。 10, 278–296. doi: 10.1007/s11469-011-9318-5
Kuss,DJ和Griffiths,MD(2011b)。 在线社交网络和成瘾:对心理学文献的回顾。 诠释。 J. Environ。 RES。 公共卫生 8,3528-3552。 doi:10.3390 / ijerph8093528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Kuss,DJ和Griffiths,MD(2012)。 互联网和游戏成瘾:神经影像学研究的系统性文献综述。 脑科学。 2,347-374。 doi:10.3390 / brainsci2030347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Kuss,DJ,Griffiths,MD,Karila,M。和Billieux,J。(2014)。 网络成瘾:过去十年对流行病学研究的系统回顾。 CURR。 医药。 德。 20,4026-4052。 doi:10.2174 / 13816128113199990617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Laier,C.,Pawlikowski,M.,Pekal,J.,Schulte,FP和Brand,M。(2013)。 网络成瘾:在观看色情内容时经历过性唤起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性接触会产生影响。 J. Behav。 冰火。 2,100-107。 doi:10.1556 / JBA.2.2013.002
Laier,C.,Pekal,J。和Brand,M。(2014)。 互联网色情的异性恋女性用户的网络成瘾可以通过满足假设来解释。 Cyberpsychol。 Behav。 SOC。 网络。 17,505-511。 doi:10.1089 / cyber.2013.0396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Lee,YH,Ko,CH和Chou,C。(2014)。 重新访问台湾学生的网络成瘾:对学生的期望,在线游戏和在线社交互动进行横断面比较。 J. Abnorm。 儿童心理学。 doi:10.1007 / s10802-014-9915-4 [打印前的电子版]。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Leung,L。(2004)。 互联网的网络属性和诱人属性是在线活动和网络成瘾的预测因素。 Cyberpsychol。 Behav。 7,333-348。 doi:10.1089 / 109493104129130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刘易斯,BA和奥尼尔,香港(2000)。 与大学生饮酒问题有关的酒精预期和社会赤字。 冰火。 Behav。 25, 295–299. doi: 10.1016/S0306-4603(99)00063-5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Lopez-Fernandez,O。,Honrubia-Serrano,ML,Gibson,W。和Griffiths,MD(2014)。 英国青少年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对成瘾症状的探索。 COMPUT。 哼。 Behav。 35,224-233。 doi:10.1016 / j.chb.2014.02.042
Lortie,CL和Guitton,MJ(2013)。 网络成瘾评估工具:维度结构和方法论状态。 瘾 108,1207-1216。 doi:10.1111 / add.12202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Lu,H.-Y。 (2008)。 寻求感情,互联网依赖和在线人际欺骗。 Cyberpsychol。 Behav。 11,227-231。 doi:10.1089 / cpb.2007.005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Meerkerk,GJ,Van Den Eijnden,RJJM,Franken,IHA和Garretsen,HFL(2010)。 强制性的互联网使用与奖励和惩罚的敏感性以及冲动性有关吗? COMPUT。 哼。 Behav。 26,729-735。 doi:10.1016 / j.chb.2010.01.009
Meerkerk,GJ,Van Den Eijnden,RJJM和Garretsen,HFL(2006)。 预测强制性的互联网使用:这完全是关于性的! Cyberpsychol。 Behav。 9,95-103。 doi:10.1089 / cpb.2006.9.95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Meerkerk,GJ,Van Den Eijnden,RJJM,Vermulst,AA和Garretsen,HFL(2009)。 强制性互联网使用量表(CIUS):一些心理测量属性。 Cyberpsychol。 Behav。 12,1-6。 doi:10.1089 / cpb.2008.0181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Morahan-Martin,J。和Schumacher,P。(2000)。 大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发生率及相关因素。 COMPUT。 哼。 Behav。 16, 13–29. doi: 10.1016/S0747-5632(99)00049-7
Morahan-Martin,J。和Schumacher,P。(2003)。 互联网的孤独和社交用途。 COMPUT。 哼。 Behav。 19, 659–671. doi: 10.1016/S0747-5632(03)00040-2
Moscovitch,DA,Hofmann,SG和Litz,BT(2005)。 自我建构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性别特定的互动。 个人。 Individ。 DIF。 38,659-672。 doi:10.1016 / j.paid.2004.05.021
Muthén,L。和Muthén,B。(2011)。 Mplus。 洛杉矶:Muthén和Muthén。
Newton,NC,Barrett,EL,Swaffield,L。和Teesson,M。(2014)。 与青少年酒精滥用相关的危险认知:道德脱离,酒精预期和感知的自我调节功效。 冰火。 Behav。 39,165-172。 doi:10.1016 / j.addbeh.2013.09.030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Niemz,K.,Griffiths,MD和Banyard,P。(2005)。 大学生病态互联网使用的流行程度以及与自尊,一般健康问卷(GHQ)和去抑制的相关性。 Cyberpsychol。 Behav。 8,562-570。 doi:10.1089 / cpb.2005.8.562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Nimrod,G。(2011)。 老年人在线社区的有趣文化。 老年病学 51,226-237。 doi:10.1093 / geront / gnq084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Pawlikowski,M.,Altstötter-Gleich,C。和Brand,M。(2013)。 Young的网络成瘾测试的简短版本的验证和心理测量属性。 COMPUT。 哼。 Behav。 29,1212-1223。 doi:10.1016 / j.chb.2012.10.014
Pawlikowski,M.,Nader,IW,Burger,C.,Biermann,I.,Stieger,S。和Brand,M。(2014)。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 它是一个多维而不是一维构造。 冰火。 RES。 理论 22,166-175。 doi:10.3109 / 16066359.2013.793313
Podsakoff,PM,Mackenzie,SM,Lee,J。和Podsakoff,NP(2003)。 行为研究中的常见方法差异:对文献的批判性回顾和推荐的补救措施。 J. Appl。 心理学。 88,879-903。 doi:10.1037 / 0021-9010.88.5.879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Pontes,HM,Griffiths,MD和Patrão,IM(2014)。 在教育环境中儿童和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和孤独:一项实证研究。 Aloma:Revista de Psicologia,Ciènciesdel'Educacióide l'Esport 32,91-98。
Purty,P.,Hembram,M。和Chaudhury,S。(2011)。 网络成瘾:当前的影响。 Rinpas J. 3,284-298。
Robinson,TE和Berridge,KC(2000)。 成瘾的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激励敏感化观点。 瘾 95, 91–117. doi: 10.1046/j.1360-0443.95.8s2.19.x
Robinson,TE和Berridge,KC(2001)。 激励敏感和成瘾。 瘾 96,103-114。 doi:10.1046 / j.1360-0443.2001.9611038.x
Robinson,TE和Berridge,KC(2008)。 成瘾的激励致敏理论:一些当前的问题。 PHILOS。 跨。 R. Soc。 林斯顿。 B Biol。 科学。 363,3137-3146。 doi:10.1098 / rstb.2008.009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罗森伯格,M。(1965)。 社会与青少年自我形象。 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Schulz,P.,Schlotz,W。和Becker,P。(2004)。 Trierer Inventar zum Chronischen Stress(TICS)。 哥廷根:Hogrefe。
Schwarzer,R。和耶路撒冷,M。(1995)。 “广义自我效能量表” 健康心理学中的措施:用户的投资组合。 因果和控制信念,编辑J. Weinman,S。Wright和M. Johnston(温莎,英国:NFER-NELSON),35-37。
Sprock,J。和Yoder,CY(1997)。 妇女与抑郁症:APA工作组报告的最新情况。 性别角色 36,269-303。 doi:10.1007 / BF02766649
Starcevic,V。(2013)。 网络成瘾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吗? 奥斯特。 NZJ精神病学 47,16-19。 doi:10.1177 / 000486741246169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Tang,J.,Yu,Y.,Du,Y.,Ma,Y.,Zhang,D。和Wang,J。(2014)。 青少年网络用户中网络成瘾的流行及其与压力性生活事件和心理症状的关联。 冰火。 Behav。 39,744-747。 doi:10.1016 / j.addbeh.2013.12.010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撒切尔,A.,Wretschko,G。和Fridjhon,P。(2008)。 在线流程体验,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拖延。 COMPUT。 哼。 Behav。 24,2236-2254。 doi:10.1016 / j.chb.2007.10.008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Tonioni,F.,Mazza,M.,Autullo,G.,Cappelluti,R.,Catalano,V.,Marano,G.,et al。 (2014)。 网络成瘾是一种与病态赌博不同的精神病理状态吗? 冰火。 Behav。 39,1052-1056。 doi:10.1016 / j.addbeh.2014.02.016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Turel,O。和Serenko,A。(2012)。 社交网站享受的好处和危险。 欧元。 J. Inf。 SYST。 21,512-528。 doi:10.1057 / ejis.2012.1
Turel,O.,Serenko,A。和Giles,P。(2011)。 整合技术成瘾和使用:对在线拍卖用户的实证调查。 MIS夸脱。 35,1043-1061。
Velicer,WF(1976)。 从部分相关矩阵确定组件的数量。 Psychometrika 41,321-327。 doi:10.1007 / BF02293557
Vuori,S。和Holmlund-Rytkönen,M。(2005)。 55 +人为互联网用户。 营销Intell。 计划。 23,58-76。 doi:10.1108 / 02634500510577474
Weinstein,A。和Lejoyeux,M。(2010)。 网络成瘾或过度使用互联网。 上午。 J.药物滥用酒精 36,277-283。 doi:10.3109 / 00952990.2010.491880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Whang,LSM,Lee,S。和Chang,G。(2003)。 互联网过度用户的心理状况:网络成瘾的行为抽样分析。 CyberPsychol。 Behav。 6,143-150。 doi:10.1089 / 109493103321640338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Widyanto,L。和Griffiths,MD(2006)。 “网络成瘾”:批判性评论。 诠释。 J. Ment。 健康瘾君子。 4, 31–51. doi: 10.1007/s11469-006-9009-9
Widyanto,L.,Griffiths,MD,Brunsden,V。和Mcmurran,M。(2008)。 互联网相关问题量表的心理测量属性:试点研究。 诠释。 J. Ment。 健康瘾君子。 6, 205–213. doi: 10.1007/s11469-007-9120-6
Widyanto,L。和McMurran,M。(2004)。 网络成瘾测试的心理测量属性。 Cyberpsychol。 Behav。 7,443-450。 doi:10.1089 / cpb.2004.7.44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Winkler,A.,Dörsing,B.,Rief,W.,Shen,Y。和Glombiewski,JA(2013)。 网络成瘾的治疗:荟萃分析。 临床。 心理学。 启示录 33,317-329。 doi:10.1016 / j.cpr.2012.12.005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Wölfling,K.,Beutel,ME和Müller,KW(2012)。 构建标准化临床访谈以评估网络成瘾:首次发现有关AICA-C的有用性。 J. Addict。 RES。 疗法。 S6:003. doi: 10.4172/2155-6105.S6-003
Wölfling,K.,Müller,K。和Beutel,M。(2010)。 “诊断措施:用于评估互联网和电脑游戏成瘾的规模(AICA-S),” 计算机游戏添加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编辑D.Mücken,A。Teske,F。Rehbein和B. Te Wildt(Lengerich:Pabst Science Publishers),212-215。
Xu,ZC,Turel,O。和Yuan,YF(2012)。 青少年在线游戏成瘾:动机和预防因素。 欧元。 J. Inf。 SYST。 21,321-340。 doi:10.1057 / ejis.2011.56
Yang,C.,Choe,B.,Baity,M.,Lee,J。和Cho,J。(2005)。 SCL-90-R和16PF的高中生使用过多的资料。 能够。 J.精神病学 50,407-414。
Yee,N。(2006)。 玩在线游戏的动机。 Cyberpsychol。 Behav。 9,772-775。 doi:10.1089 / cpb.2006.9.772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Young,KS(1996)。 上瘾的互联网使用:一个打破刻板印象的案例。 心理学。 众议员。 79,899-902。 doi:10.2466 / pr0.1996.79.3.899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Young,KS(1998)。 陷入网络:如何识别网络成瘾的迹象 - 以及恢复的成功策略。 纽约:John Wiley&Sons,Inc.
Young,KS(2004)。 网瘾:一种新的临床现象及其后果。 上午。 Behav。 科学。 48,402-415。 doi:10.1177 / 0002764204270278
Young,KS(2007)。 网络成瘾者的认知行为疗法:治疗结果和影响。 Cyberpsychol。 Behav。 10,671-679。 doi:10.1089 / cpb.2007.9971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Young,KS(2011a)。 CBT-IA:第一个解决网络成瘾问题的治疗模式。 J. Cogn。 疗法。 25,304-312。 doi:10.1891 / 0889-8391.25.4.304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Young,KS(2011b)。 “互联网成瘾客户的临床评估” 网络成瘾:评估和治疗手册和指南,由KS Young和C. Nabuco De Abreu编辑。 (新泽西州霍博肯: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34。
Young,KS(2013)。 使用CBT-IA与因特网成瘾患者的治疗结果。 J. Behav。 冰火。 2,209-215。 doi:10.1556 / JBA.2.2013.4.3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Young,KS,Pistner,M.,O'Mara,J。和Buchanan,J。(1999)。 网络障碍:新千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Cyberpsychol。 Behav。 2,475-479。 doi:10.1089 / cpb.1999.2.475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Young,KS,Yue,XD和Ying,L。(2011)。 “网络成瘾的流行率估计和病因模型” 网络成瘾,由KS Young和CN Abreu编辑。 (新泽西州霍博肯:约翰·威利父子公司),3–18。
Zhou,Y.,Lin,F.-C.,Du,Y.-S.,Qin,L.-D.,Zhao,Z.-M.,Xu,J.-R。和Lei,H。 (2011)。 网络成瘾中的灰质异常: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研究。 欧元。 J. Radiol。 79,92-95。 doi:10.1016 / j.ejrad.2009.10.025
Pubmed摘要 | 发布全文 | CrossRef全文 | Google Scholar
关键词:网络成瘾,人格,精神病理学,应对,认知行为疗法
引用:品牌M,Laier C和Young KS(2014)网络成瘾:应对方式,预期和治疗意义。 面前。 心理学。 5:1256。 doi:10.3389 / fpsyg.2014.01256
收到:25 August 2014; 接受:16十月2014;
在线发布:11 November 2014。
编辑:
Ofir Turel,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富勒顿和美国南加州大学
点评人:
Aviv M. Weinstein,哈达萨医疗组织,以色列
达里亚乔安娜库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版权所有©2014 Brand,Laier和Young。 这是一份根据条款分发的开放获取文章 知识共享署名许可(CC BY)。 允许在其他论坛中使用,分发或复制,前提是原始作者或许可人被记入贷方,并且根据公认的学术惯例引用本期刊中的原始出版物。 不允许使用,分发或复制,不符合这些条款。
*通讯:Matthias Brand,普通心理学系:认知,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Forsthausweg 2,47057杜伊斯堡,德国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