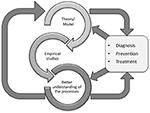面前。 Psychol。,20十月2017 |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1853
- 1互联网成瘾中心,Russell J. Jandoli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圣文德大学,Olean,纽约,美国
- 2普通心理学:德国埃森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行为成瘾研究的认知和中心
- 3Erwin L. Hahn德国埃森磁共振成像研究所
虽然,它尚未被正式认可为可诊断的临床实体,但互联网游戏障碍(IGD)已包含在第III部分中,供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DSM-5中进一步研究(APA,2013)。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所有年龄段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面临非常真实的,有时甚至是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由于在线游戏上瘾。 本文总结了IGD的一般方面,包括诊断标准和分类为成瘾性疾病的论据,包括神经生物学研究的证据。 基于先前的理论考虑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考察了最近提出的一个模型 - 人 - 情感 - 认知 - 执行(I-PACE)模型的相互作用,用于激发未来的研究和开发IGD的新治疗方案。 I-PACE模型是一个理论框架,通过观察易感因素,主持人和调解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减少执行功能和减少决策来解释网络成瘾的症状。 最后,本文讨论了当前针对网络成瘾的认知 - 行为疗法(CBT-IA)的治疗方案如何与I-PACE模型中假设的过程相适应。
介绍
网络成瘾首先在1995中根据600案例研究确定,该案例研究涉及遭受教育,学业,财务或关系问题甚至失业的人,因为他们失去了对互联网使用的控制(年轻,1996, 1998a,b)。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网络成瘾研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 该领域的其他先驱者包括Drs等心理学家。 David Greenfield和Marissa Hecht Orzack(Greenfield,1999; Orzack,1999)和Mark Griffiths博士(例如, 格里菲斯和亨特,1998; 格里菲斯,1999)。 实证研究开始出现,重点关注流行率和精神病理学合并症与自我选择的样本,多个案例研究,以及对网络成瘾的几种特定心理社会相关性的探索,如人格和社会方面(例如, Armstrong等,2000; Moran-Martin和Schumacher,2000; Shapira等,2000; 周,2001; Kubey等人,2001; Caplan,2002)。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障碍,这些早期的科学研究(1995-2005)创造了关于该主题的新的理论和全球模型(例如, 格里菲斯,1995, 2005; 戴维斯,2001),旨在总结过度在线活动的主要症状和潜在过程。
在亚洲文化中,与任何其他文化相比,处理互联网使用的问题似乎更为重要(可能的原因在例如 Montag等,2016)。 然而,在2006中,美国通过第一次全国性研究发现,超过10%的美国人至少满足一个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标准(Aboujaoude等,2006)。 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过去15年中,出现了新的Internet应用程序,例如Facebook,Twitter和WhatsApp,它们使技术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Montag等,2015并模糊上瘾和功能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区别。
早在2008,专业人士就最新版诊断和统计手册(DSM; Block,2008)。 随着越来越多的关注,讨论和研究,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最近在第III部分中包含了互联网游戏障碍(IGD),以便在DSM-5中进一步研究(APA,2013)。 这对研究领域有重大影响,因为通过在IGM-5中列出IGD进行进一步研究,APA希望鼓励对IGD进行研究,以确定这种情况是否具有临床相关性,因此应该作为可诊断的疾病纳入即将发布的版本中。帝斯曼。 这一发展也很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所有年龄段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面临非常真实的,有时甚至是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由于在线游戏上瘾(年轻,2004, 2015)。 DSM-5标准包括持续使用在线游戏,通常与其他玩家一起使用,导致临床上显着的损伤或困扰,如12月期间的五个(或更多)以下条件所示:
•专注于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被取消时的退出症状。
•容忍因为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互联网游戏。
•未成功控制参与互联网游戏的尝试。
•由于互联网游戏以及除网络游戏之外的其他爱好和娱乐失去兴趣。
•尽管存在心理问题,仍继续过度使用网络游戏。
•该人欺骗了家庭成员,治疗师或其他有关互联网游戏数量的人。
•使用网络游戏来逃避或缓解消极情绪(例如,无助感,内疚感,焦虑感)。
•由于参与网络游戏,此人已经危及或失去了重要的关系,工作,教育或职业机会。
DSM-5指出,只有没有赌博特征的在线游戏与此提议的疾病相关,因为在线赌博包含在DSM-5赌博障碍标准中。 在教育,学术或商业环境中使用互联网进行必要的活动也不包括在IGD的DSM-5标准中。 此外,IGD不包括其他娱乐或社交互联网使用。 同样,不包括过度使用含有色情内容的互联网应用程序。 随着将赌博障碍转移到物质相关和成瘾性疾病的类别,DSM-5强调物质使用障碍和行为成瘾之间的相似之处。 然而,就网络成瘾而言,仍有争议地讨论成瘾概念是否适合描述该现象。 一些作者认为,在提到不受控制和过度的在线行为时,一个更为中性的术语(并不直接暗示行为会让人上瘾)会更好。Kardefelt-Winther,2014, 2017)。 另一方面,有许多研究,特别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发现了物质使用障碍和IGD(以及其他类型的互联网使用障碍)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证明了分类成瘾的合理性(Weinstein等,2017)。 然而,在使用问卷调查的行为层面上,一些研究表明,与行为成瘾和物质使用障碍之间的重叠相比,不同类型的行为成瘾(即赌博障碍和不同类型的网络成瘾)之间存在较大的重叠(Sigerson等,2017),代表一种独特的行为成瘾类别。 人们必须注意到,不同类型的物质使用障碍之间也存在显着差异(Shmulewitz等,2015),然而它们在DSM-5的一个类别中分类。 我们这里不会对这个主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将成瘾概念用作研究IGD和其他使用障碍的一个框架是有意义的。 当然,重要的是要另外测试替代框架,例如冲动控制障碍或强迫症的概念,以更好地理解IGD的真实性质。 应用不同的理论框架来研究IGD很重要,因为一些作者认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个问题是许多研究缺乏理论背景(Billieux等人,2015; Kardefelt-Winther等,2017)。 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即进行理论驱动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过度在线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我们认为成瘾概念是一个重要的框架,可以激发理论驱动学习。 成瘾概念也有助于根据物质使用障碍领域的经验创建特定的治疗方案。 我们还认为,互联网使用障碍的特定理论模型已经存在(参见下文),但它们必须在实证研究中更加集中地用于测试特定的理论假设并提高这些模型的有效性。 作为术语的最后一点,我们想评论“沉迷于互联网”和“沉迷于互联网”之间的重要区别,Starcevic已经指出了这一点。Starcevic,2013; Starcevic和Billieux,2017)。 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互联网只是一种为特定在线行为提供许多可能性的媒介,并且了解互联网上不同类型行为背后的具体机制至关重要。 然而,鉴于网络成瘾这一术语被该领域的许多作者广泛使用,我们在提及更普遍的过度在线行为时仍使用该术语。 与DSM-5术语一致,我们还使用术语互联网使用障碍,然后应根据特定的在线行为(例如,使用购物网站,使用色情等)来指定。
网络游戏障碍的神经生物学:简要总结
由于对整个网络成瘾和特定IGD的科学研究在过去的20年中迅速增长,因此解决这一临床现象的神经生物学相关性变得非常普遍。 关于IGD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知识包括遗传贡献,神经化学改变以及IGD的结构和功能大脑相关性的证据(Weinstein等,2017).
对网络成瘾和IGD的潜在遗传贡献与多巴胺有关(Han等人,2007),血清素(Lee等人,2008)和胆碱能系统(Montag等,2012)。 研究表明,尽管各研究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差异,但网络成瘾症状的差异可能与遗传因素的差异高达48%(Deryakulu和Ursavas,2014; Li等人,2014; Vink等人,2016; Hahn等,2017)。 然而,结果与已知的遗传对其他心理障碍(包括物质使用障碍)的贡献相当(Egervari等,2017)和赌博障碍(Nautiyal等人,2017)。 对网络成瘾的遗传贡献很可能与其他心理特征相互作用,例如人格,例如,已经表明自我导向性(Hahn等,2017)。 自我导向是互联网使用障碍背景下最相关的人格特质之一(Sariyska等,2014; Gervasi等,2017).
关于IGD的大脑相关性,大多数发现显示IGD和其他行为成瘾(例如,赌博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的共性。 关于IGD神经影像学发现的最新综述 Weinstein等人。 (2017) 强调目前使用神经影像学技术的研究类似于物质使用障碍研究的结果(例如,腹侧纹状体的参与作为渴望的神经相关性和前额脑区域的功能障碍代表抑制性控制的缺陷)。 我们这里仅总结一些神经影像学发现的例子。 例如,通过研究灰质密度 袁等人。 (2011)。 他们报告说,在患有网络成瘾的青少年样本中,前额区域的灰质体积减少,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眶额皮质。 这些前额叶减少与成瘾持续时间相关,表明这些大脑变化可以反映抑制控制的减少。 已经报道了IGD /网络成瘾受试者的抑制和认知控制功能障碍,这与物质使用障碍中发现的相似(见 Brand等,2014b)。 还报告了前额叶灰质的减少 翁等人。 (2013),与网络成瘾测试所测量的症状严重程度相关(年轻,1998a)。 另一方面,也有证据表明过度游戏玩家的灰质体积较高,例如腹侧纹状体(Kühn等人,2011)。 腹侧纹状体的较高体积可以反映更高的奖励敏感性,这也已经在具有物质使用障碍的个体中显示(参见 Goldstein和Volkow,2002; Volkow等人,2012)。 然而,最近在Facebook使用过多的背景下报道了腹侧纹状体灰质体积减少的相反发现(Montag等,2017a)。 鉴于该领域的研究在样本构成,研究设计和分析方面没有直接可比性,因此需要进行更系统的研究,比较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障碍。
在考虑这些疾病的功能性大脑相关性时,物质使用障碍,赌博障碍和IGD的共性变得更加明显。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当面对与游戏相关的线索时腹侧纹状体的活动更大(Thalemann等人,2007; Ko等人,2009; Ahn等人,2015; Liu等人,2016)。 这一发现也与酒精使用障碍患者在面对酒精相关线索时观察到的结果相当(例如, Braus等,2001; Grüsser等,2004)。 另一个例子是当具有IGD的受试者执行执行执行功能的任务时的前额皮质活动。 已显示前额叶活动 - 取决于分析中包括的任务和前额区域 - 与健康受试者相比增加和减少(例如, Dong等人,2012, 2013, 2015; Brand等,2014b).
总之,有一些证据表明前额叶和边缘大脑区域特别涉及IGD现象和一般的网络成瘾(参见 Kuss和Griffiths,2012; Meng等人,2015; Sepede等,2016),并且 - 如最近所示 - 在社交网站的上瘾使用中(他等人,2017)。 这些大脑异常与IGD中的神经心理功能相对应,特别是在执行和认知控制任务中表现降低(参见 Brand等,2014b, 2016),也与物质使用障碍中报道的那些相当,例如酒精使用障碍患者(周等人,2014)。 神经心理学研究结果符合成瘾的双重过程理论(参见 Bechara,2005; Everitt和Robbins,2016),最近已被指定用于IGD(Schiebener和Brand,2017)以及社交网站的上瘾使用(Turel和Qahri-Saremi,2016)。 大多数神经生物学研究结果支持将IGD视为成瘾性疾病的观点,该观点促进了DSM-5类别物质相关和成瘾性疾病的分类(Weinstein等,2017).
IGD领域未来几年神经科学研究的挑战在于显示这些大脑变化是否与治疗成功相关,在可逆性方面,还在于这些大脑异常是否可以预测治疗成功。
理论模型
自早期病例报告20多年前以来,许多研究已经调查了互联网使用障碍的临床现象,特别关注IGD。 如上所述,一些作者声称大多数关于IGD和其他行为成瘾的临床研究缺乏明确的理论框架(Billieux等人,2015; Kardefelt-Winther等,2017)。 如上所述,我们同意许多关于IGD的精神病合并症或人格相关性的研究没有考虑明确的理论背景。 然而,我们也认为网络成瘾的理论和理论模型已经存在,这可能有助于激发关于IGD临床现象潜在机制的明确假设。 早期的模型侧重于网络成瘾的组成部分,例如组件模型 格里菲斯(2005),这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例如通过激发理论驱动的评估工具的发展(Kuss等人,2013)。 然而,组件模型相当概括了症状,而不是互联网使用障碍中涉及的心理过程。 几年后,人们提出了两种最近的IGD或网络成瘾模型。 该模型由 Dong和Potenza(2014) 侧重于IGD的认知行为机制,还包括一些治疗建议。 他们争辩说,尽管长期的负面后果,寻找即时奖励在IGD中起着核心作用。 这种决策风格被认为与寻求动机(渴望)相互作用,这意味着体验快乐的动力和减少负面情感状态的动力。 寻求动机被认为是由监测和其他执行功能控制,并且有研究显示IGD患者的抑制控制减少(Argyriou等,2017)。 在他们的模型中, Dong和Potenza(2014) 还包括治疗的潜在选择。 认知增强疗法和经典认知行为疗法被认为可用于改变功能失调的决策风格,并有助于抑制对动机寻求的抑制控制。 基于正念的压力减少被认为通过减少缓解压力和消极情感状态的动机,有助于减少寻求动机。 认知偏差修改可以影响奖励感觉,这也有助于寻求动机。 总之,模型由 Dong和Potenza(2014) 包括认知(执行)组成部分,决策风格和动机组成部分在解释IGD时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不同治疗干预的组合来解决。
另外还介绍了IGD和网络成瘾的另一种模式 Brand等。 (2014b)。 该模型基本上由三个不同的部分(甚至三个不同的模型)组成:第一个描述互联网的功能/健康使用,第二个模型旨在描述非特定/广义互联网使用障碍的发展和维持,第三个模型部分描述了涉及特定类型的使用中的疾病的潜在机制,例如IGD。 互联网的功能使用模型强调,许多应用程序可用于娱乐,逃避现实和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厌恶情境。 然而,有人认为,功能/健康使用的特点是互联网用于满足某些需求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目标后立即停止。 第二部分,非特异性/广义互联网使用障碍的模型,也认为应对机制是重要的。 然而,假设与功能失调的应对方式和某些互联网使用预期的相互作用中的精神病理学脆弱性(例如,抑郁,社交焦虑)解释了从功能/健康使用向不受控制的过度使用互联网的转变,而没有清晰的首选应用程序。 这种观点符合其他研究人员对互联网或其他媒体有问题的使用的假设,特别关注使用媒体进行应对和逃避现实的作用(Kardefelt-Winther,2014, 2017)。 已经使用大量非临床样本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易感因素(抑郁,社交焦虑)与介质功能失调的应对和使用预期在解释未指定/广义互联网使用障碍症状中的相互作用(Brand等,2014a)。 第三部分在工作中 Brand等。 (2014b) 旨在解释特定的互联网使用障碍,例如IGD。 除了上述脆弱性因素以及功能失调的应对和预期之外,该模型还表明,使用特定应用的特定动机会导致特定的互联网使用障碍。 我们还认为,在成瘾过程中,抑制性控制的减少会导致决策失调,偏好短期奖励选择,导致过度使用特定应用(参见决策和执行功能研究的引文)上文提到的)。
两年后,人们提出了修订的特定互联网使用障碍模型。 基于新的理论考虑和最近的实证结果,介绍了特定互联网使用障碍的人 - 情感 - 认知 - 执行(I-PACE)模型的相互作用(Brand等,2016)。 I-PACE模型是用于假设过程的理论框架,该过程是对某些Internet应用程序(如游戏,赌博,色情内容,购物和通讯)上瘾的开发和维护的基础。 I-PACE模型由过程模型组成,包括易变变量以及主持人和中介人变量。 更好地了解(可变)调节和中介变量的作用可以直接启发治疗(请参阅下一节关于治疗的意义)。 特定的互联网使用障碍被认为是神经生物学和心理成分(易感变量)与调节变量(例如应对方式和与互联网相关的认知和注意偏见)以及中介变量(例如情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情境触发因素的认知和认知反应,以及减少的抑制控制。 由于适应过程,这些联系在成瘾过程中变得更强。 一个人的核心特征(例如,性格,心理病理学)与情感方面(例如,渴望,体验愉悦或减少负面情绪的动机),认知方面(例如,应对方式,内隐的积极联想),执行功能的主要相互作用I-PACE模型总结了在特定互联网使用障碍的开发和维护过程中做出的决策,以及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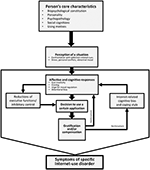
图1。 减少版本的I-PACE模型(Brand等,2016).
I-PACE模型旨在总结那些与所有类型的特定互联网使用障碍相关的过程。 因此,没有包括游戏特定元素。 虽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我们认为游戏可以提供许多奖励,这有助于在奖励条件提示反应和渴望的基础上发展IGD。 许多游戏都设计得足够复杂,具有挑战性,并允许玩家取得成就,从而保持游戏。 个人方面,例如实现目标,以及社交互动,例如与其他玩家交流,是许多游戏的基本要素,并有助于在游戏时获得“最佳体验”或流动感(Choi和Kim,2004)。 获得高分的可能性是最容易识别的钩子之一,因为玩家不断尝试击败高分,这可以在大多数游戏中无休止地完成。 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中,玩家尝试获得更高的状态(“升级”),更多的力量以及其他玩家的认可。 成就,或更详细的机制作为成就的一个子维度,再加上逃避现实,确实是全面研究中游戏相关问题的明确预测因素。 Kuss等人。 (2012)。 网络游戏的另一个钩子是许多玩家对他们的游戏角色产生情感依恋(年轻,2015)。 除此之外,许多游戏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开始或维持社交关系(科尔和格里菲斯,2007)。 玩家经常与其他玩家交朋友,而这些朋友甚至可能要求玩家继续玩游戏或增加玩游戏的时间。 事实上,即使在自我射击游戏中,大多数玩家也会报道团队游戏。 例如,在自我射击游戏玩家的个性研究中 蒙塔格等人。 (2011),90%的610参与者报告说他们经常作为一名队员参赛。 许多游戏玩家的社交互动的相关性也在一项纵向研究中进行了调查 Billieux等。 (2013)。 他们发现,与合作相结合的发现是网络游戏快速发展的最重要预测因素。 这些结果与提出的三因子模型(包括10子因子)一致 怡(2006)。 该模型表明,成就,社交和沉浸感是玩家动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许多研究中已经检验了该模型,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验证了主要假设。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最近的一项研究(De Grove等,2016)开发了一个衡量玩在线游戏(或广义上的数字游戏)的动机的量表。 他们还发现了一系列因素,包括表现,社交方面,以及他们所谓的叙事(与发现领域相当)以及其他因素(例如,逃避现实,习惯)是玩在线游戏的主要动机(另见 Demetrovics等,2011)。 总之,玩游戏最相关的动机是成就(或表现),社交互动和逃避/发现。 尽管这些具体的动机并未明确地包含在I-PACE模型中,但它们代表了使用某种应用的动机,其在模型中用“使用动机”来表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发展IGD。 此外,动机可以解释为什么其他人出现互联网色情使用障碍的症状,可能是因为他们可能具有更高的性兴奋性或更高的特质性动机(Laier等,2013; Laier和Brand,2014; Stark等,2015)。 这些使用动机被认为是人的核心特征,因此是IGD或其他互联网使用障碍的发展和维持的重要预测指标。 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些动机不会直接影响IGD的发展。 虽然,IGD更有可能在具有与游戏相关的动机非常高的个人中发展,但在玩游戏时会遇到的满足感或消极增援与使用动机相一致,这会促进与游戏相关的内隐认知的发展(例如,注意偏见,与游戏的隐式积极关联)以及特定于游戏的显式使用期望。 这些认知方面使得它在个人面临与游戏相关的刺激的情况下,或在日常生活中情绪低落或压力大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提示反应性和渴望。 这些动机相互作用,游戏时满足感的传递以及与游戏相关的情况下内隐和外显认知的变化以及情感反应被认为是IGD发展和维持的主要过程(见图 1).
尽管I-PACE模型是假设的,并且必须详细调查关于可能成为特定互联网使用障碍的发展和维持的机制的假设,但可以规定对治疗的影响。 在下一节中,我们总结了一些最近的治疗方法,并将它们与I-PACE模型中总结的理论假设联系起来。 然而,I-PACE模型仅旨在解释IGD和其他因特网使用障碍的症状的发展和维持。 值得注意的是,IGD(或者通常玩电脑和视频游戏,至少如果游戏是在不离开家或不进行体育锻炼的情况下进行的)通常与其他一些(生理)影响有关,例如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这与降低睡眠质量和过度消费甜饮料有关(Turel等,2017)。 在IGD治疗中不应忽视这些额外的问题。 但是,这些附加主题未包含在I-PACE模型中,因此未在治疗影响部分中介绍。
治疗意义
虽然IGD的性质和潜在的心理机制仍有争议(见引言中的简要讨论),但这种现象的临床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有必要提供适当的治疗干预措施,以帮助客户避免游戏或减少游戏行为。 在本文中,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对IGD临床干预的系统评价,包括心理治疗和药物干预,可在其他地方找到(Kuss和Lopez-Fernandez,2016; King等人,2017; Nakayama等人,2017).
大多数研究已经研究了认知 - 行为疗法(CBT)在治疗一般的网络成瘾或特别是IGD中的应用(Dong和Potenza,2014; King和Delfabbro,2014),第一个荟萃分析发现CBT在提到在线行为所花费的时间时表现优于其他心理治疗(Winkler等,2013).
我们在这里专注于一种特定类型的干预,CBT用于网络成瘾(CBT-IA),以及这种治疗方法如何与I-PACE模型相关。 CBT-IA专门用于通过将经典CBT元素与特定的互联网相关问题相结合来治疗网络成瘾(年轻,2011)。 CBT-IA由三个阶段组成:(1)行为修改,(2)认知重组和(3)危害减少。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将更详细地解释这三个阶段。 在128患有网络成瘾的患者的结果研究中(年轻,2013),CBT-IA被发现可有效减轻症状,改变适应不良的认知,并管理与网络成瘾症状相关的潜在的个人和情境因素。 最近,CBT-IA模型可以应用于IGD病例。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针对在线游戏指定CBT-IA的互联网相关元素(例如,关于自己的互联网使用的适应不良认知)(年轻,2013).
最一致的是,治疗应首先评估客户当前对所有屏幕和技术的使用情况。 虽然,摄入量评估通常是全面的,并且涵盖了精神疾病的大多数相关症状,包括成瘾行为,IGD症状或其他类型的互联网使用障碍,但由于其新颖性,经常在临床常规访谈中被忽略。 一些治疗师不熟悉IGD和其他类型的网络成瘾,因此可能忽略了这种疾病的潜在征兆。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临床医生应常规评估总体上过度使用Internet以及特别是IGD过度使用和不受控制的潜在症状。
随着所有互联网应用程序的持续可用性,与每个客户单独开发有关互联网使用和使用其他媒体或屏幕技术(包括视频游戏)的清晰结构化恢复计划非常重要。 患有食物成瘾或暴饮暴食行为的个体通过客观指标(例如热量摄入量和体重减轻量)评估其恢复成功的部分。 与此类比,IGD患者的治疗应客观地通过减少在线时间,数字节食和禁止与有问题的在线应用程序的任何接触来测量部分恢复成功,在IGD的情况下是特定的在线游戏。 这就是一些作者所说的数字营养,这是Jocelyn Brewer在2013中创造的概念(http://www.digitalnutrition.com.au/)。 然而,数字营养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所有屏幕技术或互联网应用,而是使用互联网和媒体设备的健康,功能,平衡的方式。
数字营养更是一种开发健康和功能性技术用途的预防策略。 当个人患有IGD症状的全部情况时,治疗应有助于患者戒除游戏,并仅适度地将互联网用于其他目的。 这是最困难的步骤,这是名为行为修改的CBT-IA的第1阶段。 治疗师需要监视客户的互联网和技术使用情况,并帮助客户重新调整与媒体和屏幕技术的联系。 这也意味着刺激和情境控制,包括指导客户在家改变情境,使他们变得更容易不使用游戏。 例如,这可以包括计算机重组。 随后的行为成为进一步的治疗目标,例如能够完成日常活动,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习惯,并与其他人(例如,在体育馆或俱乐部里)在互联网上度过时间或专心于其他爱好。 拥有IGD的个人需要在玩游戏之前重新参与他们喜欢的活动,或者寻找新的活动,作为放弃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学习热爱。 合并I-PACE模型和CBT-IA时,CBT-IA的第1阶段(行为修改)主要针对情况方面以及使用特定应用程序的决策(请参见图XNUMX)。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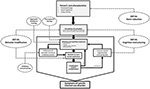
图2。 将CBT-IA元件和进一步治疗方法整合到I-PACE模型中(Brand等,2016).
具体来说,利用I-PACE模型和CBT-IA模型,评估客户的应对方式和与互联网相关的认知偏见以及对游戏的情感和认知反应非常重要。 这是CBT-IA阶段2:认知重构的主题。 患有IGD的人患有认知扭曲,使他们沉迷于游戏。 例如,他们可能会感到孤独,躁动甚至沮丧,但是当他们在玩在线游戏时,在线角色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感到自信并深受喜爱。 自尊心低的客户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受欢迎,但给人的印象是,游戏是提高自尊的一种方式。 CBT-IA使用认知重组来打破这种适应不良的认知和互联网使用预期的模式(年轻,2013)。 “认知结构的调整通过挑战客户,并在许多情况下,重新书写客户背后的消极思想,有助于将客户的认知和情感“置于显微镜下”。年轻,2013,p。 210)。 CBT-IA可以帮助IGD患者了解他们正在使用在线游戏来避免负面情绪或逃避现实,并且他们认为与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其他活动相比,他们在玩游戏时会感受到更积极的感受。 这对于客户来说有时很难,但理解和改变这些适应不良的想法对治疗成功很重要。 同样,I-PACE和CBT-IA模型的重点是检查通过玩游戏体验满足的机制,以及在现实生活中不满足的需求以及通过过度玩耍来补偿的需求(年轻,2013; Brand等,2016).
与客户进行认知重组对于帮助IGD的客户重新评估他或她对情境和感受的解释是否合理有效也是有用的。 例如,使用在线游戏作为一种感觉更好的生活方式并感受到强大,强大和公认的方式的客户将开始意识到他或她正在使用在线游戏来满足不满意的需求。他或她的现实生活。 在此背景下,CBT-IA帮助客户制定更多功能性和健康性的应对策略,以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消极情绪,并寻找健康的方法来增强自尊和自我效能,并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
正如在许多成瘾中一样,那些看到他们在线游戏存在问题的玩家中最常见的反应是“内疚和清除周期”。至少对于大多数游戏玩家来说,真正的恢复包括查看潜在的动机和预期。游戏习惯。 治疗还必须帮助客户识别,处理和治疗与IGD共同发生的潜在问题,这是CBT-IA阶段3:减少伤害的主要方面。 特别是,应该治疗潜在的抑郁和社交焦虑。
CBT-IA可以通过最近提出的神经认知训练来补充,这些训练已经在物质使用障碍的背景下得到积极评估。 一个例子是对内隐认知的再训练,这可能会在遇到渴望时导致回避而非接近倾向(Wiers等,2011; Eberl等,2013a,b)。 有意再培训计划(例如, Schoenmakers等,2010; Christiansen等人,2015)可能有助于提高客户的抑制力(例如, Houben和Jansen,2011; Houben等,2011; Bowley等人,2013)。 这可以通过使用具有与成瘾相关的刺激的Go / No-Go任务来完成。 然而,未来的研究必须证明这些技术有助于增加IGD背景下的抑制性控制。 提示暴露疗法(Park等,2015)可以用于减少经验丰富的强度(Pericot-Valverde等,2015),这与IGD目前的神经影像学发现一致(Zhang等人,2016).
I-PACE模型关于与IGD和其他互联网使用障碍的发展和维持有关的潜在过程的主要假设以及一些最相关的治疗技术(CBT-IA和其他方法)的综合假设 2。 虽然这个数字集中在I-PACE模型上,但它也广泛适用于其他作者提出的假设(Dong和Potenza,2014)。 如上所述,在他们的模型中, Dong和Potenza(2014) 他认为,认知行为疗法和认知增强疗法对于改变决策风格和增强对使用网络游戏动机的抑制控制很有用。 认知偏见修改与CBT-IA中所谓的认知重组类似,有助于影响客户的期望,使其在玩游戏时获得奖励(周等人,2012)。 未来的研究还应该调查媒介互联网本身在帮助客户方面的作用。 最近的一些研究集中在可以指导客户日常生活的应用程序上,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压力(例如,通过正念减轻压力)或更好地应对负面情绪,但此类应用程序还可以跟踪客户在网上的时间这也可能对治疗有用。 有关心理信息学对网络成瘾治疗的贡献的最新概述,请参见 蒙塔格等人。 (2017b).
为什么在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合并互联网使用障碍(如I-PACE)和现有治疗方法(如CBT-IA)的理论模型是有帮助的? 我们认为理论模型的目标是总结疾病发展和维持的主要过程。 这些模型可用于指定假设过程的研究假设。 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疾病现象学中涉及的核心过程,我们可以检查这些过程是否通过现有的治疗方法得到解决,如果不是,那么当前的治疗方案如何通过其他特定技术得到补充。 另一方面,对治疗方法疗效的研究也可以激发疾病的理论模型。 如果我们看到例如认知重组对客户特别有用,那么显然认知过程(例如,预期)在维持该病症中特别重要,并且如果他们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些过程,则可以检查现有模型。 总之,理论模型和治疗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 这种关系总结在图中 3.
在合并I-PACE和CBT-IA模型时,我们看到CBT-IA的三个主要阶段特别针对那些在I-PACE模型中被认为是缓和和中介变量的变量。 然而,我们看到,很可能CBT-IA可以通过其他技术(图中较小的椭圆)进行补充 2)。 I-PACE和CBT-IA模型也可用于开发临床实践的新评估工具。 例如,如果我们在实证研究中看到,互联网使用预期在解释互联网使用障碍症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Brand等,2014a)我们认为认知重组对于改变这些预期是有用的(年轻,2013),使用经过验证的工具来评估临床实践的互联网使用预期是有帮助的。 将此问题纳入预防计划也会有所帮助。 数字 3 旨在总结理论(以及因此对过程的实证研究)和临床实践(包括诊断,预防和治疗)之间的双向关系。 鉴于理论模型和治疗方法(以及诊断和预防)从来都不是最终的或完美的,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两个领域如何能够成功地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以提高有效性和疗效。
结论
本文回顾了与IGD发展相关的最相关的神经生物学研究,IGD和其他特定互联网使用障碍的发展和维持的一些理论模型,以及使用I-PACE和CBT-IA模型对成瘾客户的治疗影响。
目前的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IGD和其他行为成瘾(例如,赌博障碍)以及物质使用障碍具有几个相似之处。 可以在分子水平(例如,遗传贡献),神经电路(例如,包括腹侧纹状体和前额皮质的若干部分的多巴胺额纹状环)和行为水平(包括隐性(例如,注意偏倚)和显性)中看到相似性。情绪和认知(Brand等,2016)。 随着我们向前发展,IGD的诊断从临床,教育和文化背景中产生了一些影响。
临床上,应该在咨询培训,学校和机构中应用更多的关注和培训。 鉴于其新颖性,一些临床医生仍然忽视了IGD的症状。 因此,临床医生必须接受评估程序的培训,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实践中是否存在过度和不受控制的互联网使用。 此外,临床医生应接受IGD治疗和其他类型的互联网使用障碍的培训。 必须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治疗方案。 事实上,虽然早期结果数据显示CBT-IA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客户维持健康的在线常规,但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检查其他治疗方式,如团体治疗,家庭治疗和 体内 咨询,看看他们的综合治疗效果。
如果IGD确实被视为一种疾病,这也会对学校系统产生影响,制定屏幕智能政策,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IGD问题的影响。 让教育工作者接受有关如何识别最易患IGD风险的学生的培训将会很有帮助。 学校管理者制定政策可以帮助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技术,以防止IGD发生,策略可能包括在课堂上使用有限的屏幕,没有游戏政策,以及鼓励学校的社交俱乐部。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IGD研究中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存在一些局限性。 关于分类,诊断标准和手段,概念化作为成瘾或其他类型的疾病,以及旨在理解IGD和其他互联网使用障碍的性质的研究的许多其他未解决的问题或挑战,一直存在争论。 因此,只要将使用整合到日常生活中而不会经历严重的负面后果,就必须不对一般的互联网或特别是游戏的健康和平衡使用进行过度病理治疗。
理论模型可以激发调查IGD和其他互联网使用障碍性质的实证研究。 在未来的研究中使用这些模型来阐明明确的研究假设是很重要的。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系统地解决一致性和不同性的有效性。 虽然I-PACE模型的理论背景是成瘾框架,但我们还必须考虑实证研究中的其他理论方法,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潜在的机制。 未来的研究将证明成瘾框架的哪些方面以及其他理论的哪些部分在解释IGD方面是有效的。 关于疾病的理论模型可能会激发治疗方法,但前提是这些理论模型是有效的并且已经过经验检验。 未来IGD研究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将现有的关于疾病潜在心理机制的理论假设与治疗和预防技术相结合。 理论和治疗的灵感应该是双向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心理机制和治疗研究的研究相互作用。
作者贡献
列出的所有作者都对该作品做出了实质性,直接和智力的贡献,并批准其出版。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研究是在没有任何可被解释为潜在利益冲突的商业或金融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
参考资料
Aboujaoude,E.,Koran,LM,Gamel,N.,Large,MD和Serpe,RT(2006)。 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的潜在标志:2,513成人的电话调查。 CNS光谱。 11,750-755。 doi:10.1017 / S1092852900014875
Ahn,HM,Chung,HJ和Kim,SH(2015)。 在游戏体验之后改变了对游戏线索的大脑反应。 Cyberpsychol。 Behav。 SOC。 网络。 18,474-479。 doi:10.1089 / cyber.2015.0185
APA(2013)。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5th Edition。 华盛顿特区:APA。
Argyriou,E.,Davison,CB和Lee,TTC(2017)。 响应抑制和互联网游戏障碍:一项荟萃分析。 冰火。 Behav。 71,54-60。 doi:10.1016 / j.addbeh.2017.02.026
Armstrong,L.,Phillips,JG和Saling,LL(2000)。 更重的互联网使用的潜在决定因素。 诠释。 J. Hum。 COMPUT。 梭哈。 53,537-550。 doi:10.1006 / ijhc.2000.0400
Bechara,A。(2005)。 决策,冲动控制和抵抗药物意志力的丧失:一种神经认知的观点。 纳特。 神经科学。 8,1458-1463。 doi:10.1038 / nn1584
Billieux,J.,Schimmenti,A.,Khazaal,Y.,Maurage,P。和Heeren,A。(2015)。 我们是否过度日常生活? 行为成瘾研究的可行蓝图。 J. Behav。 冰火。 4,119-123。 doi:10.1556 / 2006.4.2015.009
Billieux,J.,Van Der Linden,M.,Achab,S.,Khazaal,Y.,Paraskevopoulos,L.,Zullino,D.,et al。 (2013)。 你为什么玩魔兽世界? 深入探索在艾泽拉斯虚拟世界中进行在线游戏和游戏内行为的自我报告动机。 COMPUT。 哼。 Behav。 29,103-109。 doi:10.1016 / j.chb.2012.07.021
Block,JJ(2008)。 DSM-V的问题:网络成瘾。 上午。 J.精神病学 165,306-307。 doi:10.1176 / appi.ajp.2007.07101556
Bowley,C.,Faricy,C.,Hegarty,B.,Johnston,S.,Smith,JL,Kelly,PJ,et al。 (2013)。 抑制性控制训练对饮酒,隐性酒精相关认知和脑电活动的影响。 诠释。 J. Psychophysiol。 89,342-348。 doi:10.1016 / j.ijpsycho.2013.04.011
Brand,M.,Laier,C.,and Young,KS(2014a)。 网络成瘾:应对方式,预期和治疗意义。 面前。 心理学。 5:1256。 doi:10.3389 / fpsyg.2014.01256
Brand,M.,Young,KS和Laier,C。(2014b)。 前额控制和网络成瘾:理论模型和神经心理学和神经影像学发现的回顾。 面前。 哼。 神经科学。 8:375。 doi:10.3389 / fnhum.2014.00375
Brand,M.,Young,KS,Laier,C.,Wölfling,K。和Potenza,MN(2016)。 整合关于特定互联网使用障碍的发展和维持的心理和神经生物学考虑因素:人 - 情感 - 认知 - 执行(I-PACE)模型的相互作用。 神经科学。 Biobehav。 启示录 71,252-266。 doi:10.1016 / j.neubiorev.2016.08.033
Braus,DF,Wrase,J.,Grüsser,S.,Hermann,D.,Ruf,M.,Flor,H.,et al。 (2001)。 酒精相关刺激激活戒酒酗酒中的腹侧纹状体。 J. Neural Transm。 108,887-894。 doi:10.1007 / s007020170038
Caplan,SE(2002)。 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心理健康:基于理论的认知 - 行为测量工具的发展。 COMPUT。 人类行为 18, 553–575. doi: 10.1016/S0747-5632(02)00004-3
Choi,D。和Kim,J。(2004)。 为什么人们继续玩在线游戏:寻找关键设计因素以提高客户对在线内容的忠诚度。 Cyberpsychol。 Behav。 7,11-24。 doi:10.1089 / 109493104322820066
Chou,C。(2001)。 台湾大学生互联网大量使用和成瘾:在线访谈研究。 Cyberpsychol。 Behav。 4,573-585。 doi:10.1089 / 109493101753235160
Christiansen,P.,Schoenmakers,TM和Field,M。(2015)。 不太满足于眼睛:重新评估成瘾中注意力偏见的临床相关性。 冰火。 Behav。 44,43-50。 doi:10.1016 / j.addbeh.2014.10.005
Cole,H。和Griffiths,MD(2007)。 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玩家的社交互动。 Cyberpsychol。 Behav。 10,575-583。 doi:10.1089 / cpb.2007.9988
戴维斯,RA(2001)。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 - 行为模型。 COMPUT。 人类行为 17, 187–195. doi: 10.1016/S0747-5632(00)00041-8
De Grove,F.,Cauberghe,V。和Van Looy,J。(2016)。 开发和验证用于衡量玩数字游戏的个人动机的工具。 媒体心理学。 19,101-125。 doi:10.1080 / 15213269.2014.902318
Demetrovics,Z.,Urbán,R.,Nagygyörgy,K.,Farkas,J.,Zilahy,D.,Mervó,B.,et al。 (2011)。 你为什么玩? 开发在线游戏问卷(MOGQ)的动机。 Behav。 RES。 方法 43, 814–825. doi: 10.3758/s13428-011-0091-y
Deryakulu,D。和Ursavas,Ö。 F.(2014)。 遗传和环境对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的影响:一项双胞胎研究。 COMPUT。 人类行为 39,331-338 doi:10.1016 / j.chb.2014.07.038
Dong,G.,Devito,EE,Du,X。和Cui,Z。(2012)。 “网络成瘾症”中的抑制性抑制受损: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 精神病学 203,153-158。 doi:10.1016 / j.pscychresns.2012.02.001
Dong,G.,Hu,Y.,Lin,X。和Lu,Q。(2013)。 是什么让网络成瘾者继续在线玩,即使面临严重的负面后果? fMRI研究的可能解释。 生物学。 心理学。 94,282-289。 doi:10.1016 / j.biopsycho.2013.07.009
Dong,G.,Lin,X,Hu,Y.,Xie,C。和Du,X。(2015)。 执行控制网络和奖励网络之间的不平衡功能链接解释了网络游戏障碍中的在线游戏寻求行为。 科学。 众议员。 5:9197。 doi:10.1038 / srep09197
Dong,G。和Potenza,MN(2014)。 网络游戏障碍的认知行为模型:理论基础和临床意义。 J. Psychiatr。 RES。 58,7-11。 doi:10.1016 / j.jpsychires.2014.07.005
Eberl,C.,Wiers,RW,Pawelczack,S.,Rinck,M.,Becker,ES和Lindenmeyer,J。(2013a)。 酒精依赖中的方法偏差修改:临床效果是否复制,对谁来说效果最好? 开发。 COGN。 神经科学。 4,38-51。 doi:10.1016 / j.dcn.2012.11.002
Eberl,C.,Wiers,RW,Pawelczack,S.,Rinck,M.,Becker,ES和Lindenmeyer,J。(2013b)。 实施酗酒方法偏差再培训。 需要多少个会话? 醇。 临床。 进出口。 RES。 38,587-594。 doi:10.1111 / acer.12281
G.Egervari,R.Ciccocioppo,Jentsch,JD和YL.Hurd(2017)。 塑造成瘾的脆弱性–行为,神经回路和分子机制的贡献。 神经科学。 Biobehav。 启。 doi:10.1016 / j.neubiorev.2017.05.019。 [印刷前的电子版]。
Everitt,BJ和Robbins,TW(2016)。 吸毒成瘾:用十年的习惯来改变习惯和强迫行为。 Annu。 Rev. Psychol。 67,23-50。 doi:10.1146 / annurev-psych-122414-033457
Gervasi,AM,La Marca,L.,Costanzo,A.,Pace,U.,Guglielmucci,F。和Schimmenti,A。(2017)。 人格和网络游戏障碍:对近期文献的系统评价。 CURR。 冰火。 众议员。 4, 293–307. doi: 10.1007/s40429-017-0159-6
Goldstein,RZ和Volkow,ND(2002)。 药物成瘾及其潜在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前额皮质受累的神经影像学证据。 上午。 J.精神病学 159,1642-1652。 doi:10.1176 / appi.ajp.159.10.1642
格林菲尔德,D。(1999)。 虚拟成瘾:帮助Netheads,Cyberfreaks和爱他们的人。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新的Harbinder出版物。
Griffiths,MD(1995)。 技术成瘾。 临床。 心理学。 论坛 76,14-19。
Griffiths,MD(1999)。 网瘾:事实还是虚构? 心理学家 12,246-250。
格里菲斯(2005)。 生物心理社会框架内的成瘾的“成分”模型。 J. Subst。 使用 10,191-197。 doi:10.1080 / 14659890500114359
Griffiths,MD和Hunt,N。(1998)。 青少年对电脑游戏的依赖。 心理学。 众议员。 82,475-480。 doi:10.2466 / pr0.1998.82.2.475
Grüsser,SM,Wrase,J.,Klein,S.,Hermann,D.,Smolka,MN,Ruf,M.,et al。 (2004)。 提示诱导的纹状体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与戒断酗酒者随后的复发有关。 精神药理学 175, 296–302. doi: 10.1007/s00213-004-1828-4
Hahn,E.,Reuter,M.,Spinath,FM和Montag,C。(2017)。 网络成瘾及其方面:遗传学的作用以及与自我指导的关系。 冰火。 Behav。 65,137-146。 doi:10.1016 / j.addbeh.2016.10.018
Han,DH,Lee,YS,Yang,KC,Kim,EY,Lyoo,IK和Renshaw,PF(2007)。 多巴胺基因和奖励依赖于青少年过度的互联网视频游戏。 J. Addict。 医学。 1, 133–138. doi: 10.1097/ADM.0b013e31811f465f
他,Q。,Turel,O。和Bechara,A。(2017)。 与社交网站(SNS)成瘾相关的脑解剖变化。 科学。 众议员。 23:45064。 doi:10.1038 / srep45064
Houben,K。和Jansen,A。(2011)。 训练抑制控制。 抵抗甜蜜诱惑的食谱。 食欲 56,345-349。 doi:10.1016 / j.appet.2010.12.017
Houben,K.,Nederkoorn,C.,Wiers,RW和Jansen,A。(2011)。 抵制诱惑:通过训练反应抑制来减少酒精相关的影响和饮酒行为。 药物酒精依赖。 116,132-136。 doi:10.1016 / j.drugalcdep.2010.12.011
Kardefelt-Winther,D。(2014)。 对网络成瘾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论批评:针对互补性互联网使用的模型。 COMPUT。 人类行为 31,351-354。 doi:10.1016 / j.chb.2013.10.059
Kardefelt-Winther,D。(2017)。 概念化互联网使用障碍:成瘾或应对过程? 精神病学临床。 神经科学。 71,459-466。 doi:10.1111 / pcn.12413
Kardefelt-Winther,D.,Heeren,A.,Schimmenti,A.,van Rooij,A.,Maurage,P.,Carras,M.,et al。 (2017)。 我们如何在不对常见行为进行病态化的情况下概念化行为成瘾? 瘾 112,1709-1715 doi:10.1111 / add.13763
King,DL和Delfabbro,PH(2014)。 网络游戏障碍的认知心理。 临床。 心理学。 启示录 34,298-308。 doi:10.1016 / j.cpr.2014.03.006
King,DL,Delfabbro,PH,Wu,AMS,Doh,YY,Kuss,DJ,Pallesen,S.,et al。 (2017)。 网络游戏障碍的治疗:国际系统评价和CONSORT评估。 临床。 心理学。 启示录 54,123-133。 doi:10.1016 / j.cpr.2017.04.002
Ko,CH,Liu,GC,Hsiao,S.,Yen,JY,Yang,MJ,Lin,WC,et al。 (2009)。 与在线游戏成瘾的游戏冲动相关的大脑活动。 J. Psychiatr。 RES。 43,739-747。 doi:10.1016 / j.jpsychires.2008.09.012
Kubey,RW,Lavin,MJ和Barrows,JR(2001)。 互联网使用和大学学业成绩减少:早期发现。 J. Commun。 51, 366–382. doi: 10.1111/j.1460-2466.2001.tb02885.x
Kühn,S.,Romanowski,A.,Schilling,C.,Lorenz,R.,Mörsen,C.,Seiferth,N。,et al。 (2011)。 视频游戏的神经基础。 译。 精神病学 15:e53。 doi:10.1038 / tp.2011.53
Kuss,DJ和Griffiths,MD(2012)。 互联网和游戏成瘾:神经影像学研究的系统性文献综述。 脑科学。 2,347-374。 doi:10.3390 / brainsci2030347
Kuss,DJ和Lopez-Fernandez,O。(2016)。 网络成瘾和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对临床研究的系统评价。 世界J.精神病学 6,143-176。 doi:10.5498 / wjp.v6.i1.143
Kuss,DJ,Louws,J。和Wiers,RW(2012)。 在线游戏成瘾? 动机预测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中令人上瘾的游戏行为。 Cyberpsychol。 Behav。 SOC。 网络。 15,480-485。 doi:10.1089 / cyber.2012.0034
Kuss,DJ,Shorter,GW,van Rooij,AJ,Griffiths,MD和Schoenmakers,TM(2013)。 使用简约的互联网成瘾组件模型评估网络成瘾。 初步研究。 诠释。 J.心理健康瘾君子。 12, 351–366. doi: 10.1007/s11469-013-9459-9
Laier,C。和Brand,M。(2014)。 从认知 - 行为角度看有助于网络成瘾的因素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考虑。 性别。 冰火。 Compul。 21,305-321。 doi:10.1080 / 10720162.2014.970722
Laier,C.,Pawlikowski,M.,Pekal,J.,Schulte,FP和Brand,M。(2013)。 网络成瘾:在观看色情内容时经历过性唤起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性接触会产生影响。 J. Behav。 冰火。 2,100-107。 doi:10.1556 / JBA.2.2013.002
Lee,YS,Han,DH,Yang,KC,Daniels,MA,Na,C.,Kee,BS,et al。 (2008)。 抑郁症喜欢5HTTLPR多态性的特征和过度互联网用户的气质。 J.影响。 Disord。 109,165-169。 doi:10.1016 / j.jad.2007.10.020
Li,M.,Chen,J.,Li,N。和Li,X。(2014)。 对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的双重研究:其遗传性和遗传关联以及努力控制。 双胞胎 哼。 遗传学。 17,279-287。 doi:10.1017 / thg.2014.32
Liu,L.,Yip,SW,Zhang,JT,Wang,LJ,Shen,ZJ,Liu,B.,et al。 (2016)。 在网络游戏障碍中的线索反应期间激活腹侧和背侧纹状体。 冰火。 生物学。 22,791-801。 doi:10.1111 / adb.12338
Meng,Y.,Deng,W.,Wang,H.,Guo,W。和Li,T。(2015)。 网络游戏障碍患者的前额叶功能障碍: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的荟萃分析。 冰火。 生物学。 20,799-808。 doi:10.1111 / adb.12154
Montag,C.,Błaszkiewicz,K.,Sariyska,R.,Lachmann,B.,Andone,I.,Trendafilov,B.,et al。 (2015)。 21st世纪的智能手机使用:谁在WhatsApp上活跃? BMC Res。 笔记 8,331。 doi:10.1186 / s13104-015-1280-z
Montag,C.,Duke,É。,Sha,P.,Zhou,M.,Sindermann,C。和Li,M。(2016)。 接受电源距离会影响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的倾向吗? 来自跨文化研究的证据。 亚太区。 精神病学 8,296-301。 doi:10.1111 / appy.12229
Montag,C.,Flierl,M.,Markett,S.,Walter,N.,Jurkiewicz,M。和Reuter,M。(2011)。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玩家的网络成瘾和个性。 J. Media Psychol。 23, 163–173. doi: 10.1027/1864-1105/a000049
Montag,C.,Kirsch,P.,Sauer,C.,Markett,S。和Reuter,M。(2012)。 CHRNA4基因在网络成瘾中的作用:病例对照研究。 J. Addict。 医学。 6, 191–195 doi: 10.1097/ADM.0b013e31825ba7e7
Montag,C.,Markowetz,A.,Blaszkiewicz,K.,Andone,I.,Lachmann,B.,Sariyska,R。,et al。 (2017a)。 Facebook在智能手机上的使用量和核心的灰质量。 Behav。 Brain Res。 329,221-228。 doi:10.1016 / j.bbr.2017.04.035
Montag,C.,Reuter,M。和Markowetz,A。(2017b)。 “心理信息学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包括新的证据,”in 网络成瘾,编辑C. Montag和M. Reuter(Cham;瑞士:Springer国际出版社),221-229。
Morahan-Martin,J。和Schumacher,P。(2000)。 大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发生率及相关因素。 COMPUT。 人类行为 16, 13–29. doi: 10.1016/S0747-5632(99)00049-7
Nakayama,H.,Mihara,S。和Higuchi,S。(2017)。 网络使用障碍的治疗和危险因素。 精神病学临床。 神经科学。 71,492-505。 doi:10.1111 / pcn.12493
Nautiyal,KM,Okuda,M.,Hen,R。和Blanco,C。(2017)。 赌博障碍:对动物和人类研究的综合评论。 安。 纽约阿卡德。 科学。 1394,106-127。 doi:10.1111 / nyas.13356
Orzack,M。(1999)。 电脑成瘾:它是真的还是虚拟的? HARV。 换货。 健康Lett。 15:8。
Park,CB,Park,SM,Gwak,AR,Sohn,BK,Lee,JY,Jung,HY,et al。 (2015)。 反复接触虚拟赌博线索对赌博冲动的影响。 冰火。 Behav。 41,61-64。 doi:10.1016 / j.addbeh.2014.09.027
Pericot-Valverde,I.,García-Rodríguez,O.,Gutiérrez-Maldonado,J。和Secades-Villa,R。(2015)。 个别变量与线索暴露治疗中的渴望减少有关。 冰火。 Behav。 49,59-63。 doi:10.1016 / j.addbeh.2015.05.013
Sariyska,R.,Reuter,M.,Bey,K.,Sha,P.,Li,M.,Chen,YF,et al。 (2014)。 自尊,人格和网络成瘾:跨文化比较研究。 个人。 Individ。 DIF。 61-62,28-33。 doi:10.1016 / j.paid.2014.01.001
Schiebener,J。和Brand,M。(2017)。 互联网游戏障碍和其他类型的互联网使用障碍的决策和相关过程。 CURR。 冰火。 众议员。 4,262-271。 doi:10.1007 / s40429-017-0156-9
Schoenmakers,TM,de Bruin,M.,Lux,IF,Goertz,AG,Van Kerkhof,DH和Wiers,RW(2010)。 抑制性酒精中毒患者注意偏倚改良训练的临床效果。 药物酒精依赖。 109,30-36。 doi:10.1016 / j.drugalcdep.2009.11.022
Sepede,G.,Tavino,M.,Santacroce,R.,Fiori,F.,Salerno,RM和Di Giannantonio,M。(2016)。 年轻人网络成瘾的功能磁共振成像。 世界J. Radiol。 8,210-225。 doi:10.4329 / wjr.v8.i2.210
Shapira,NA,Goldsmith,TD,Keck,PE,Khosla,UM和McElroy,SL(2000)。 有互联网使用问题的个人的精神病学特征。 J.影响。 Disord。 57, 267–272. doi: 10.1016/S0165-0327(99)00107-X
Shmulewitz,D.,Greene,ER和Hasin,D。(2015)。 物质使用障碍的共性和差异:现象学和流行病学方面。 醇。 临床。 进出口。 RES。 39,1878-1900。 doi:10.1111 / acer.12838
Sigerson,L.,Li,AY,Cheung,MWL和Cheng,C。(2017)。 检查常见的信息技术成瘾及其与非技术相关成瘾的关系。 COMPUT。 人类行为 75,520-526。 doi:10.1016 / j.chb.2017.05.041
Starcevic,V。(2013)。 网络成瘾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吗? Austr。 NZJ精神病学 47,16-19。 doi:10.1177 / 0004867412461693
Starcevic,V。和Billieux,J。(2017)。 网络成瘾的构成是反映单个实体还是频谱障碍? 临床。 神经精神科 14,5-10。
Stark,R.,Kagerer,S.,Walter,B.,Vaitl,D.,Klucken,T。和Wehrum-Osinsky,S。(2015)。 特质性动机问卷:概念和验证。 J.性。 医学。 12,1080-1091。 doi:10.1111 / jsm.12843
Thalemann,R.,Wölfling,K。和Grüsser,SM(2007)。 过度游戏玩家对计算机游戏相关线索的特定提示反应。 Behav。 神经科学。 121,614-618。 doi:10.1037 / 0735-7044.121.3.614
Turel,O。和Qahri-Saremi,H。(2016)。 社交网站的有问题使用:双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前因和后果。 J.管理。 通知。 SYST。 33,1087-1116。 doi:10.1080 / 07421222.2016.1267529
Turel,O.,Romashkin,A。和Morrison,KM(2017)。 这是一个将儿童和青少年的视频游戏,睡眠质量,甜饮料消费和肥胖联系起来的模型。 临床。 奥贝斯。 7,191-198。 doi:10.1111 / cob.12191
Vink,JM,van Beijsterveldt,TC,Huppertz,C.,Bartels,M。和Boomsma,DI(2016)。 青少年强制性互联网使用的遗传性。 冰火。 生物学。 21,460-468。 doi:10.1111 / adb.12218
Volkow,ND,Wang,GJ,Fowler,JS和Tomasi,D。(2012)。 人脑中的成瘾电路。 Annu。 Rev. Pharmacol。 毒理学。 52,321-336。 doi:10.1146 / annurev-pharmtox-010611-134625
Weinstein,A.,Livny,A。和Weizman,A。(2017)。 互联网和游戏障碍大脑研究的新进展。 神经科学。 Biobehav。 启示录 75,314-330。 doi:10.1016 / j.neubiorev.2017.01.040
Weng,CB,Qian,RB,Fu,XM,Lin,B.,Han,XP,Niu,CS,et al。 (2013)。 网络游戏成瘾中的灰质和白质异常。 欧元。 J. Radiol。 82,1308-1312。 doi:10.1016 / j.ejrad.2013.01.031
Wiers,RW,Eberl,C.,Rinck,M.,Becker,ES和Lindenmeyer,J.(2011)。 重新训练自动动作倾向可以改变酒精中毒患者的饮酒偏向,并改善治疗效果。 心理学。 科学。 22,490-497。 doi:10.1177 / 0956797611400615
Winkler,A.,Dörsing,B.,Rief,W.,Shen,Y。和Glombiewski,JA(2013)。 网络成瘾的治疗:荟萃分析。 临床。 心理学。 启示录 33,317-329。 doi:10.1016 / j.cpr.2012.12.005
Yee,N。(2006)。 玩在线游戏的动机。 Cyberpsychol。 Behav。 9,772-775。 doi:10.1089 / cpb.2006.9.772
Young,KS(1996)。 上瘾的互联网使用:一个打破刻板印象的案例。 心理学。 众议员。 79,899-902。 doi:10.2466 / pr0.1996.79.3.899
Young,KS(1998a)。 陷入网络:如何识别网络成瘾的迹象 - 以及恢复的成功策略。 纽约州纽约:John Wiley&Sons,Inc.
Young,KS(1998b)。 网瘾:一种新的临床疾病的出现。 Cyberpsychol。 Behav。 3,237-244。 doi:10.1089 / cpb.1998.1.237
Young,KS(2004)。 网络成瘾:一种新的临床现象及其后果。 上午。 Behav。 科学。 48,402-415。 doi:10.1177 / 0002764204270278
Young,KS(2011)。 CBT-IA:第一个解决网络成瘾问题的治疗模式。 J. Cogn。 疗法。 25,304-312。 doi:10.1891 / 0889-8391.25.4.304
Young,KS(2013)。 使用CBT-IA与因特网成瘾患者的治疗结果。 J. Behav。 冰火。 2,209-215。 doi:10.1556 / JBA.2.2013.4.3
Young,KS(2015)。 视频游戏:娱乐还是成瘾? 精神科时代成瘾和物质滥用特别报告32,UBM Medica网络,27-31。 在线提供: http://www.psychiatrictimes.com/special-reports
Yuan,K.,Qin,W.,Wang,G.,Zeng,F.,Zhao,L.,Yang,X。,et al。 (2011)。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微观结构异常。 PLoS ONE的 6:e20708。 doi:10.1371 / journal.pone.0020708
Zhang,JT,Yao,YW,Potenza,MN,Xia,CC,Lan,J.,Liu,L。,et al。 (2016)。 渴望行为干预对网络游戏障碍中线索诱发渴望神经基质的影响。 影像学 12,591-599。 doi:10.1016 / j.nicl.2016.09.004
Zhou,Z.,Yuan,G。和Yao,J。(2012)。 对具有网络游戏成瘾的个人的互联网游戏相关图片和执行缺陷的认知偏见。 PLoS ONE的 7:e48961。 doi:10.1371 / journal.pone.0048961
Zhou,Z.,Zhu,H.,Li,C。和Wang,J。(2014)。 互联网上瘾的人与依赖酒精的患者分享冲动和执行功能障碍。 面前。 Behav。 神经科学。 8:288。 doi:10.3389 / fnbeh.2014.00288
关键词:网络游戏障碍,网络成瘾,I-PACE模型,IGD治疗
引文:年轻KS和品牌M(2017)合并互联网游戏紊乱背景下的理论模型和治疗方法:个人视角。 面前。 心理学。 8:1853。 doi:10.3389 / fpsyg.2017.01853
收到:23 June 2017; 接受:04十月2017;
发布时间:20十月2017。
编辑:
Ofir Turel,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富勒顿,美国
点评人:
Tony Van Rooij,荷兰Trimbos研究所
Christian Montag,德国乌尔姆大学
版权所有©2017 Young and Brand。 这是一份根据条款分发的开放获取文章 知识共享署名许可(CC BY)。 允许在其他论坛中使用,分发或复制,前提是原始作者或许可人被记入贷方,并且根据公认的学术惯例引用本期刊中的原始出版物。 不允许使用,分发或复制,不符合这些条款。
*通讯:Matthias Brand, [电子邮件保护]
 金伯利S.杨
金伯利S.杨 马蒂亚斯·布兰德
马蒂亚斯·布兰德